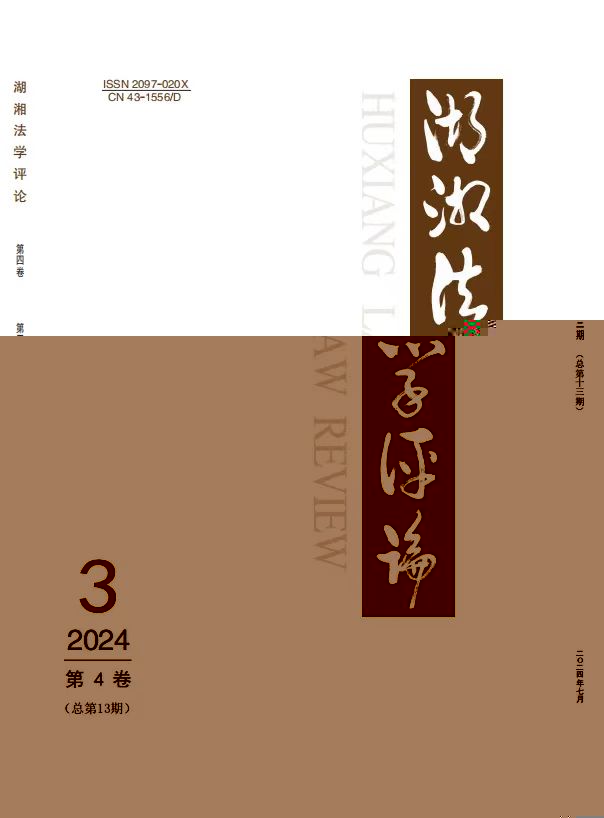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4年第3期(總第13期)“學術專論”欄目
【作者】徐國棟,法學博士,廈門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南強重點崗位教授。
【摘要】繼《奧地利民法典》于1988年采用動物非物的規定後,2000年的《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采用了植物非物的規定,兩者配合,開啟了非人類生命去客體化的思潮。1992年的《瑞士憲法》第120條賦予植物尊嚴權,也是這一思潮的體現。阿塞拜疆和瑞士的規定建立在非人類生命界的去動物中心主義的成果上。為了提高植物的法律地位,學界進行了大量的植物有智力的論證。實際上,這種論證并非植物獲得主體資格的基礎,其基礎是植物的良好生存代表的生态利益,所以應采用法益實體說來證成植物的主體資格。植物的主體化挑戰人類的食物權,可通過把植物分為自由植物和孤立植物來解決兩種需求的矛盾。孤立植物可以為人所用,但不得浪費,并且要帶着尊敬享用。如果承認植物的尊嚴權,我國《民法典》承認的植物新品種權的正當性将面臨挑戰,同樣受到挑戰的還有我國《憲法》在國有自然資源權框架下作出的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的規定。在憲法生态化的思潮下,此等規定應在調整為也包納其他權屬下的動植物後與我國《憲法》關于國家保護環境的責任的規定合并,并增加禁止對動植物實施任意的基因操作的規定,由此實現動植物的主體化。
【關鍵詞】植物非物;植物智力;植物的尊嚴權;《阿塞拜疆民法典》;植物的憲法地位
一
從動物非物到植物非物
1987年11月25日,海因茨·費舍爾(Heinz Fischer,1938—今)和沃爾特勞·霍瓦特(Waltraud Horvath)兩位議員向奧地利議會司法委員會提出議案,建議在《奧地利民法典》第285條新增如下附加條:“1.動物不算作物;它們受法律的特别保護。2.适用于物的規定僅在沒有不同和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才适用于動物。”奧地利議會收到這個議案後,在1988年3月3日的會議上讨論,通過票決,在修改後把上述建議轉化為立法。現在的《奧地利民法典》第285a條曰:“動物不是物;它們受特别法保護。适用于物的規定僅在沒有不同和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才适用于動物。”海因茨·費舍爾及其同事的提案理由是:在一條狗與一塊磚之間沒有法定的區别是不合理的。此語是對傳統民法客體理論不區分生命物和無生命物的深刻批判,但批判得不徹底,因為在一塊磚與一棵樹之間沒有法定的區别也不合理,狗和樹按照生物學都屬于生物,所以,費舍爾未把自己開啟的問題進行到底,提出植物非物的修法建議。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狗在受到侵犯時會叫喚,而樹不會,這正應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句話。令人欣慰的是,費舍爾未做的事情,12年後的2000年由《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做了,它規定:植物和動物不是物。它們的法律地位由專門法律确定。如果立法無專門規定,物的法律身份也适用于植物和動物。這是人類第一次在民法典中規定植物非物,而且把植物非物問題放在動物非物問題之前規定,這樣的排序允許人們推斷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确實,前者的數量要成倍地多于後者。至此,立法者在民法中把有生命物區别于無生命物的意圖基本得到貫徹。說“基本”,乃因為生命物除了動植物,還有真菌、微生物等,暫無立法者以明确的規定把它們排除出客體的行列,盡管在2018年,藍蝴蝶公司(Compagnie des Papillons Bleus)提出的《國際樹木權利公約》草案第7條要求公約的簽字國保護大真菌(Macromycètes),此條讓真菌的法律情勢問題在法律文件上現身,但未提議大真菌的主體化。
《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如何?馬修·霍爾(Matthew Hall)概括得好:《聖經》的一些段落可以說考慮了動物并指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一種可能的橫向關系,但幾乎無證據表明《聖經》曾賦予植物這樣的考慮。此語說的是在非人類生物界研究中存在的動物中心主義的起源。從這個角度看,《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是對這種主義的挑戰。
順便指出,與西方賤視植物的傳統不同,印度的耆那教比較正視植物在非人生命體系中的地位。該教認為,生命體有觸覺、味覺、嗅覺、視覺和聽覺五種感覺。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體都按照其所屬的感官的多少來分類。最低級的生命體僅有一種感官,即觸覺感受器官,植物屬此;最高級的生命體擁有所有五種感官,人類和大部分動物屬此。其他中間性的生命體要麼有觸覺、味覺兩種感覺,蚯蚓屬此;要麼有觸覺、味覺及嗅覺三種感覺,虱子屬此;要麼有觸覺、味覺、嗅覺和視覺四種感覺,蚊子屬此。這些說明見證了耆那教也賤視植物的一面,說它們是最低級的生命,但如下說明見證了該教對植物看法的另一面:禁止食用在地下生長的蔬菜和水果(根莖植物),理由是為了取得這類蔬果,人們須連根拔起植物,如此就毀壞了整個植物,并且破壞了其根部附近的微組織。此外,該教隻許在果蔬自然成熟并準備落地時才可采摘,或者等它們從樹上掉落後才采收。如此可享用植物而不害其性命。如果要從樹上直接采果,隻能采摘必要的數量,不能浪費。谷類如小麥、稻米、玉米,以及豆類等,要在作物或豆莢已幹燥且死時才能采。絕對禁止為了取得木材或作其他用途而砍樹。總之,耆那教禁止信徒在超出個人需求的情況下任意“殺戮”植物。
讓我們回到奧地利。《奧地利民法典》的上述規定開創了重設動物民法地位的動物非物模式,受到《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阿塞拜疆民法典》《摩爾多瓦民法典》《愛沙尼亞物權法》《加泰羅尼亞民法典》的追随。在學說上,上述規定引發了大量的研究。就中文世界而言,标題中包含“動物不是物”字樣的論文有3篇。但《阿塞拜疆民法典》的上述規定已誕生24年,卻未發現有哪一部民法典追随其而創立“植物非物”模式,除了一位秘魯議員為了證明在該國民法典中補立“動物非物”之類的規定的必要性而援引了上述規定,别無其他援引。在學說上,暫未發現任何專門研究。這可能是因為阿塞拜疆的國際地位不如奧地利,也可能是因為該國使用的阿塞拜疆語不如德語通行,這兩個不利因素影響了《阿塞拜疆民法典》的這一出色規定擴大影響。本文拟介紹這一規定的古今思想基礎以及類似的立法或提案,從而為植物乃至全部自然物的主體化張目。
二
植物非物,是什麼?
大哉問!《奧地利民法典》第285條附加條曾經受到類似質疑,終于催生了2012年的新《捷克民法典》第494條的規定:活動物作為有感生靈,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活動物不是物,關于物的規定僅在不違背其本性的範圍内類推适用于活動物。此條終于正面說清了動物是有感生靈。所謂有感生靈,是能感覺、察知、反應,有快樂感和痛苦感的動物。把動物界定為有感生靈,拉近了它們與人類的距離,因為人類也有苦樂等感覺,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人類就要善待動物,甚至賦予其有限主體地位。
讀者可注意到前段中的兩個詞,第一個是“它們”。我們從小就在語文課堂上知道,這個第三人稱代詞應用來指稱無生命的客體,現在确認了動物是有感生靈,再用這個詞指稱動物就不合适了,所以,有必要重用劉半農創造的“牠”字指稱動物。當然,如果證明了植物也有生命,更需要創立一個新的第三人稱代詞指代之。第二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人”,我們不得不用此詞來表征動物乃至植物,反映了我們身處的人類中心主義語言學現實。我們的語言以人類為唯一的主體,對于其他存在,隻能用拟人法指代。如果我們進入一個生态中心主義的社會,人類将和動植物平等,那時候,人稱代詞系統也将面臨變革。
2009年,以《植物對話:偷聽植物世界的秘密》(Pflflanzen Palaver,Belauschte Geheimnisse der botanischen Welt,2008)一書的作者弗洛裡安·凱什蘭(Florianne Koechlin,1948—今)為首的15位德語學人簽署的《發現植物:關于植物權利的萊瑙論文》對本節标題提出的問題作出了回答。其辭曰:植物是生物(德文為Lebewesen;英文為living being)。這一回答好生令人失望,因為植物是生物,從生物學誕生起就無人否認過。生物學研究的對象有三:動物、植物和真菌、微生物。如果這樣回答,根據《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提出的問題,可得出該款不過講了一個世人皆知的常識,故為無甚意義的結論。
無獨有偶,1994年在法國誕生,由法國樹木協會主席、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喬治·費特曼(Georges Feterman,1952—今)起草的《樹木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arbre)第1條也局部地回答了同一問題。說“局部”,因為它隻回答了植物中的一種,即樹是什麼的問題。它規定:樹木是固着的生命體,以相當的比例占據着兩種不同的環境,即大氣和土壤。土壤中的根系可以吸收水分和礦物質。樹冠生長在大氣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和太陽能。因此,樹木對地球的生态平衡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此條的第一句也令人失望,不過基本複述了樹是生物的常識。說“基本”,因為它加了“固着的”定語,樹因根而生,不能移動,移動即影響其存活。此條的其他文句,一講了樹木的“跨界”(地上和地下)生存方式;二講了其生态貢獻。隻能認為此等貢獻是樹木應被賦予權利的理由,不似動物因為其有感覺而應被賦予權利的理由。
實際上,立法者宣稱植物不是物的理由是我們人類對它們認知不夠,如果對它們亂加幹預(包括轉基因幹預),可能造成無法控制的後果,所以,人類應順應植物的自然。上引《發現植物:關于植物權利的萊瑙論文》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對植物的感知能力所知甚少。細胞和分子生物學證明了它們似乎有感知能力,但到目前為止,仍缺乏完整的證據鍊。聲稱植物沒有感知能力且感覺不到疼痛與相反的說法一樣具有推測性。所以,我們不能完全科學地理解植物的本質。這方面存在認識論上的限制。
既然人類對植物知曉不夠,隻能抛棄幹預植物的生命以達成自己目的的想法,順應植物的自然。此等順應體現為賦予植物6項權利。其一,生殖權,絕育技術和其他不育方法的唯一目的是使農作物獲得最大的産量,違反了此權;其二,自主權(獨立權),植物不是客體,不應被工具化并随意控制;其三,進化權,即植物調試自己适應環境的權利,為此要保持物種的多樣性和基因的多樣性;其四,作為種的幸存權,即要保障所有品種的植物(徐國棟按:此語應包括所謂的“有害植物”)都能幸存,實現生物多樣性;其五,在研究和開發中的受尊重權,即要求研究者和有關工業能感知目标植物的獨一無二性,帶着尊敬的态度研究之,不得無限制地把植物作為使用客體;其六,排斥專利化權,此權肯認植物并非發明,任何植物的存在都不能僅歸功于人類活動。因此,不僅應出于社會經濟原因拒絕植物專利,而且應為植物本身而拒絕之。此權的反對目标是植物新品種權。
上述6權的相對人似乎并非普通的植物所有人或占有人,而是植物的研究者和植物産品的開發商,所以,這6權依托的規範并非民法規範,而是科研-開發倫理規則。這一規則體系不同于關于動物的規則體系,後者是地道的民法規範,考慮的規制對象是動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及廣大的第三人。
那麼,弗洛裡安·凱什蘭等德語科學家為何要為植物的研究和開發設置上述限制?4位法語科學家(佩爾特、馬祖瓦耶、莫諾、吉拉爾東)合著的《植物之美》回答了此問題:人類發展到今天,已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地球上植物原有的自然分布狀況。許多植物在任意篩選種植和改良後甚至已與其原生種類毫無相似之處。這在農作物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為了片面增加産量而不斷選種和改良品種,緻使多樣化品種逐漸被單一品種替代,或者說許多老品種被單一的新品種所替代。同時,我們還正在自作聰明地對農作物進行冒險的基因實驗,而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評估此舉的長期後果。人們移動了生态效應鍊,而這一點是人們所不熟悉的,也是不能很好控制的,自然有必要格外小心。僅憑人類目前所具有的知識與智慧,還遠遠無法将植物界的奧秘窮盡。畢竟植物已在地球上繁衍了上億年,而人類對植物的系統研究則僅有300多年。绠短汲深,人類還是不要冒進為好。
拟回答本節标題提出的問題當作總結:植物是我們認識不足的對象,少知多畏,我們不能以科研的名義亂加幹預。
三
瑞士把植物權利當作憲法問題
1992年,瑞士通過全民公決修憲,新立第120條(非人類領域的基因技術),行文如下:1.應保護人類及其環境免受基因技術濫用的影響;2.聯邦應就動物、植物和其他有機物的生殖和遺傳物質的使用制定法律,在這樣做時,應考慮到被造物的尊嚴以及人、動物和環境的安全,并應保護動植物品種的基因多樣性。
此條的條名和第1款就揭示了确立動植物和其他生物的權利旨在限制基因技術的濫用。此條第2款首先把動植物和其他生物免受基因技術濫用的影響當作瑞士聯邦政府的責任而非普通民事主體的責任;其次以宗教術語“被造物”統稱動物和植物,并賦予它們尊嚴權;最後把主體(包括人和動物)和環境的安全、動植物品種的基因多樣性的保護當作規範目的。這裡的“其他有機物”至少應包括微生物,如果這一推論成立,則第120條在人類立法史上第一次把微生物作為權利主體考慮。
此條中的“被造物”的術語具有宗教性,因為根據《聖經·創世紀》的記載,上帝用6天造世間萬物。第3天造植物(青草、菜蔬、樹木);第5天造動物(水中生物及天上飛鳥);第6天造人。人、動物、植物三者,通稱為被造物(creature)。按瑞士當局的解釋,被造物包括動物、植物、真菌和微生物在内。人之所以被排除,乃因為第119條對其有專門規定:1.人類應被保護以防止輔助性醫療生殖技術和基因工程的濫用。2.聯邦應就生殖和基因物質的使用制定法律。在此方面,聯邦承擔對人的尊嚴、人格、家庭的保護并遵守以下原則:(1)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以及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材料和胚胎的幹預。(2)非人類的基因遺傳和生殖遺傳不得被移植到人類生殖遺傳領域或将二者混合。(3)隻有在有不育症或避免傳播嚴重疾病的情況下才能使用輔助性醫療生殖技術,但是不得為生育具有某些特征的兒童而進行研究;體外受精隻有在法律允許的條件下才可使用,且唯有在一定數量的卵細胞能立即被植入體内時方可進行體外受精直到胚胎期。(4)禁止捐贈胚胎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代孕。(5)禁止人類胚胎和胚胎制品的交易。(6)非經本人同意或根據法律規定,不得對個人的遺傳基因進行分析、記錄和交流。(7)每個人均有權了解有關自己的直系親屬的資料。此條與第120條平行,目的在于限制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和基因工程濫用于人類,以保障人的尊嚴。這樣,人的尊嚴和其他被造物的尊嚴就結伴受到保護。兩種尊嚴被統稱為生物的“尊嚴”。“尊嚴”指的是此等生物的内在價值,即它們為自身而存在,而不考慮它們對任何人或任何其他事物的有用性的價值。“植物”與“人”的這種結伴性是瑞士立法機關造就的。第119條的草案最初由一份消費者雜志提出,聯邦議會在把它加工為法律文本的過程中提出補充,增加第120條作為公決内容。顯然,瑞士立法機關認識到了人的尊嚴與其他被造物的尊嚴的關聯性和同質性,故安排把它們一并規定。這樣的安排為我們理解第120條提供了幫助,因為我們通常明了對人的生殖和基因進行操作的倫理風險,卻對植物等生物進行同樣的操作的倫理風險不敏感,把兩者并列規定,可加強我們對後種風險的敏感性。
至此可見,第119條和第120條的目的是禁止魯莽的基因工程,瑞士人認為這是危險的,所以設定了人的尊嚴和生物的尊嚴來對抗權力的傲慢。瑞士人認為,每一次新的基因合成引入都無異于玩生态輪盤賭,也就是說,雖然隻有很小的機會引發環境爆炸,但如果真的發生,後果可能是雷鳴般的和不可逆轉的。為了合理運用基因技術,瑞士于2022年1月頒布了《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Bundesgesetz über die Gentechnik im Ausserhuman-bereich)。該法與2011年頒布的《聯邦人類研究法》(Bundesgesetz über die Forschung am Menschen)形成配合,調整兩個領域的基因技術适用實踐。《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第1條(本法目的)規定,本法旨在:“1.保護人類、動物和環境免受基因工程的侵害;2.在基因工程的應用中為人類、動物和環境造福;3.在此背景下,本法的目的尤其在于保護人類、動物和環境的健康和安全;……5.尊重被造物的尊嚴……”本條第2款表明了立法者并不完全禁止運用基因技術的立場。第5款重申了尊重被造物的尊嚴是運用基因技術的前提條件。第8條(尊重被造物的尊嚴)第1款規定了何以構成侵害被造物的尊嚴: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對動植物的遺傳物質進行改造,不得損害生物的尊嚴。如果物種的具體特征、功能或生活方式受到嚴重損害,并且沒有任何值得保護的利益可以證明這種行為是正當的,那麼這種尊嚴就會受到侵犯。要根據動物和植物的不同來評估傷害。同條第2款規定了為達成特别值得保護的利益,可以損害被造物的尊嚴,這些利益有:(1)人類和動物健康;(2)确保充足的營養;(3)減少生态偏見;(4)維護和改善生态生活條件;(5)在經濟、社會和生态層面對社會具有實質性效用;(6)知識的增加。當然,按第3款的規定,聯邦委員會可決定在何種條件下允許在利益不平衡的情況下對遺傳材料進行特别的修改。此法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不把被造物的尊嚴設定為絕對,可以為了人的利益以及非人類動物的健康利益犧牲此等尊嚴。
《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并非無牙之虎,違反該法者,要承擔《瑞士債法典》第42~47條、第49~53條規定的損害賠償責任。嚴重的,要承擔該法第35條規定的刑事責任:三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由此,瑞士形成了保障植物權利的法網,它由《瑞士憲法》《非人類基因技術法》中的相應規定構成。這是一條公法的路徑,不同于《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的采用的私法的路徑。
四
阿塞拜疆和瑞士的規定是破除動物中心主義的成果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和《瑞士憲法》第120條外加《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的相關規定的貢獻在于承認了植物享有權利,這是破除了非人類生命領域長期存在的動物中心主義的結果。
如前所述,馬修·霍爾觀察到:《聖經》考慮了動物與人的共性,沒有證據表明《聖經》曾考慮植物與人的共性,這是宗教世界的預設。在世俗世界,自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以來的哲學思想一直賤視植物,原因在于動物有與人相似的感官,甚至有腦,而植物與人沒有這些相似性。這種傾向有人稱之為大腦沙文主義,直到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之後才逐漸被破除。達爾文于1880年與其子弗朗西斯·達爾文(Francis Darwin,1848—1925)合著了《植物運動的力量》一書,首次探讨了植物的認知。他們使用神經學描述了植物根部的敏感性,提出根尖的作用類似于某些低等動物的大腦。此等根尖對感覺作出反應以确定植物的下一個動作。結論是:植物具有最低限度的認知,許多動物甚至細菌也具有這樣程度的認知能力。
撇開非西方文化學者對植物地位的肯認不談,在達爾文之後,不少西方學者研究了植物智力問題。
2006年,意大利學者斯特凡諾·曼庫索(Stefano Mancuso,1965—今)等人(即埃裡克·D.布倫納、萊納·斯塔爾伯格、豪爾赫·維萬科、弗蘭蒂塞克·巴盧什卡、伊麗莎白·範·沃爾肯伯格)發表《植物神經生物學:植物信号的綜合觀點》一文,說明了植物如何處理從環境中獲得的信息,以最佳地發展、繁榮和繁殖的過程,從而證成了植物智力。曼庫索等指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許多人錯誤地認為智力是“使我們區别于其他生物的東西”,但如果我們将智力視為解決和克服困難的能力,植物也擁有它,正是智力使植物發展并對它們在整個個體發生過程中遇到的大多數問題作出反應。植物有自己的智力形式,植物靠它們彼此溝通,還靠它們與動物溝通。最典型、最普遍的例子是,植物利用自己果實的香味吸引動物食用并排出種子來擴大自身的傳播範圍。當然,植物為了使種子能有效傳播,讓未熟的果實不能吃,這是一種保護機制。2013年,曼庫索與亞曆山德拉·維奧拉合作,把上述成果發展成了《燦爛的綠色:植物智能的驚人曆史和科學》一書,擴展了其植物智力理論。兩位作者證明,植物除了具有視覺、嗅覺、味覺、觸覺、聽覺外,還有另外15種感覺。這樣的論證直接否定了耆那教關于植物僅有觸覺的說法。就植物的聽覺而言,曼庫索做過這樣的實驗:向某種植物發射200赫茲的聲音,然後以高速攝影機記錄植物的反應,發現植物能感受且“理解”收到的聲音。植物能知曉電流、水流聲等,與周邊環境進行交流,靠聲音來尋找合适自己生活的地方。總之,曼庫索及其合作者的著作更新了人們對植物的認識。
2008年,弗洛裡安·凱什蘭出版《植物對話:偷聽植物世界的秘密》一書。作者試圖挑戰植物都被視為機器,它們隻是根據内置程序作出行為的成見。作者介紹,有大學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用最現代的方法研究植物的語言,有的學者甚至在植物中找到神經樣結構。由此,作者成功地創造了新的植物形象。
2011年,美國學者馬修·霍爾出版了《作為人的植物:哲學性的植物學》一書。此書回顧了西方文化傳統中對非人類生命界采用動物中心主義的曆史,以及非西方文明中一些有利于植物獲得與動物同樣關注的觀點,并綜述了達爾文以來的破除動物中心主義的理論,主張将植物看成主體(person),從而把現今人與植物的工具關系轉化為尊重關系。先是減少人類對植物界的損害,進而修複已實施的損害。
2014年,英國學者安東尼·特雷瓦瓦斯(Anthony Trewavas,1939—今)出版了《植物行為和智力》一書,指出:學習、記憶和智力在植物學中不是常用術語,因為人們相信行為隻是具有神經系統的生物體的特性。但有大量證據證明植物有智力。例如,有些植物通過撞擊産生的機械刺激來探測合适的支障物;有些植物則利用反射的遠紅光或揮發性化學物質完成探測;它們還能預測未來在何處會遭遇競争與被遮擋光線,如果有必要,就采取入侵行動,率先長出枝葉占領有利位置,讓整個身體在陽光下獲得最适宜的位置。植物甚至有神經系統,植物細胞之間的離子通道,主要是鈣離子通道,就是其神經系統。特雷瓦瓦斯認為植物智力的用途之一是競争。确實,像所有生物一樣,植物必須獲得它們生長所需的資源,它們需要應對捕食者、疾病并尋找配偶,還要争奪必需品、光、礦物質、水以及空間,具有尖端生長的分枝結構是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它為植物提供了占用最大空間、獲取資源的潛力,反過來又有助于植物阻止附近競争對手獲得資源。
豌豆的智力受到學界的特别關注。以色列本·古裡安大學布勞斯坦沙漠研究所的一組科學家發表的研究結果證明,遭受幹旱的豌豆苗會将其困窘傳遞給與它共享土壤的同類植物。換句話說,它通過根向其鄰居傳遞關于幹旱開始的生化信息,促使它們作出反應。那麼,植物是如何傳遞信号的?所有植物的葉子、枝條、根、皮、果實和花朵都會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學物質,它們可能就是植物的語言。另外,豌豆還會铤而走險。為了實驗,謝梅什博士和牛津大學行為生态學家亞力克斯·卡切爾尼克種植了一些豌豆,并将豌豆根部一分為二,放進兩個花盆。其中一個花盆的營養含量是恒定的,另一個花盆的營養含量會随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當營養不足時,營養含量變化不定的花盆裡的豌豆生出了更多的根;但當營養充足時,它們更傾向于營養含量恒定的花盆。這個實驗證明:豌豆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冒險。
2013年,邁克爾·馬德爾(Michael Marder,1980—今)出版《植物思維:植物生命的哲學》一書。作者筆下的“植物思維”指植物特有的非認知、非觀念、非意象的思維方式,也可稱為“無頭思維”。非認知,指植物思維完全由遺傳和環境決定,區别于具有認知性的動物思維。非觀念也是相對于人的思維而言的。人通過感官接受刺激,将此等刺激輸入大腦進行整理,形成觀念。植物無大腦,所以其思維是非觀念的。非意象,即無須視覺形象幫助。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前,人們大多認為思維靠圖像的幫助進行,1900年左右,在德國維爾茨堡工作的一群心理學家證明,人們可以在無圖像幫助的情況下思維,此種思維即非意象的思維。馬德爾認為植物的思維屬此。總之,馬德爾超越了植物智力的言論,進入植物思維的言論,推動了植物類人化的進程。
2014年,我國學者祁雲枝出版了《植物哲學:植物讓人如此動情》一書揭示植物的智慧,例如揭示竹子具有團隊精神,群生群長,相互扶持。此書讓我國跟上了肯認植物智力的時代潮流,但與外國同道者比較起來,祁雲枝的寫作着重于外在觀察,而不是内在“解剖”(例如證明植物有智慧的原因是有類似“神經”的組織),屬于科普讀物。
以上成果,打破了非人類生命界的動物中心主義,為植物受到法律更認真的對待提供了證成。這些成果是催生2000年的《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的意識形态環境。《瑞士憲法》的規定似乎跟上述研究成果關聯不大,更多出于一種宗教感和保守性。它的藍本是更早的1980年《阿爾高州憲法》第14條:科學教學和研究以及藝術活動自由。教學與研究必須尊重被造物的尊嚴。藍本誕生的時間早于幾乎所有的證成植物主體資格的科研成果的發表時間,所以人們把《瑞士憲法》中的有利于植物的規定歸因于宗教情懷。但在2008年,瑞士聯邦倫理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針對非人類的生物技術的《關于作為生命體的植物的尊嚴的報告》,其中指出:“植物生命不僅應該得到所有其他生物的尊重,而且還具有絕對的道德價值,不能簡化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加強保育的對象了事。”從此以後,讓植物遭受“任意傷害”将在道德上受到譴責,而将植物工具化處理需要道德上的正當理由。例如:一個農夫為了其牲口果腹而打草是可接受的行為,在打完草回家的路上,他無理由地用鐮刀割了些野花,這個行動很可能就是不道德的。這個文件建立在大量的證成植物主體資格的文獻基礎上,為《瑞士憲法》第120條補上了科研基礎。
最後要提到的科研成果是美國法學家克裡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1937—2021)于1972年發表的文章《樹應該有訴訟資格嗎?邁向自然物的法律權利》,此文率先提出了自然物或無生命體的法律權利和訴訟資格的主張:既然法律可以賦予不能說話、沒有意識的國家、公司、嬰兒、無行為能力人、自治城市和大學等法律主體資格,可以為它們申請保護人或代理人,為什麼法律不能賦予自然物體以法律主體資格,不能為它們申請保護人或代理人呢?此文并未研究植物智力問題,但主張植物主體化,尤其體現在其标題中,所以筆者認為它也是去動物中心主義的重要文獻。
五
植物的民法地位重整
如前所述,《發現植物:關于植物權利的萊瑙論文》确立了6項植物權利:生殖權、自主權、進化權、作為種的幸存權、在研究和開發中的受尊重權、排斥專利化權。它們都是對抗權力的傲慢的權利,如同瑞士的經驗所證實的,它們大多不宜寫入民法典。那麼,在民法中應如何體現上述學界對植物的新認知呢?
首先要說的是,世界現有的植物種類超過40萬種,對它們一概而論是不科學的。俄羅斯學者埃皮凡諾娃(T. B. Епифанова)等人對作為民事權利客體的植物進行了分類,把它們分為自然栖息的和被孤立的兩大類。前者包括:(1)瀕危植物。列入國際紅皮書中的植物;列入俄羅斯紅皮書中的植物;特别保護自然區域(國家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自然公園、自然紀念碑、樹木公園和植物園)中的植物。(2)屬于采集對象的植物(蘑菇、藥用植物的漿果、花、草和根等)。(3)處于自然自由狀态的植物及未被一般規則定義為客體的植物。後者包括:(1)農業植物。(2)轉基因植物的母本。(3)轉基因植物。(4)觀賞植物。(5)藥用植物。
筆者理解的是,在這樣的分類中,自然栖息的植物是自由植物,人類通常不宜侵犯。被孤立的植物是人類的勞動對象,人類可帶着尊敬利用。如果這一理解未錯,可以說,埃皮凡諾娃等人的文章繼續了《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開創的問題,并把它具體化了。
在被孤立的植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業植物的民法地位重整。它們的數目不多。據研究,人類的主食主要包括14種栽培植物,而人類消耗的80%的卡路裡來自6種植物:小麥、水稻、玉米、馬鈴薯、紅薯和木薯。問題在于,既然農業植物也有生命,人類能否吃它們?
1993年的《全球倫理普世宣言》承認人類比非人類具有較大的内在價值,所以,用植物和動物果腹是更大的善,為此可以毀滅自然形态的生物。
馬德爾在其文章《吃植物合道德嗎?》中指出,問題顯然不是“我能吃植物嗎?”而是“我怎麼吃植物?”,應該是帶着尊敬去吃,有節制地去吃,不浪費。
1994年在法國誕生的《樹木權利宣言》第5條也規定: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一些樹木被種植然後被利用,不能成為受保護的樹木。但人們在利用森林或農村樹木時,必須考慮樹木的生命周期、自然更新的能力、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樣性。此條承認并非一切樹木都享受古樹名木的待遇,但樹木監護人要合理利用之。至此,我們可把《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的規定具體化一下:自由的植物不是物,孤立的植物還是物,但人們要帶着尊敬利用之。
帶着尊敬利用,是課加給植物所有人的義務,除了不浪費,還要承擔以下責任:第一,要保護古樹名木,也就是放棄對它們的經濟利用可能,維持其生态功能;第二,在為經濟目的“殺死”一棵樹後補種同樣數目的樹;]第三,當樹木自然消失時,土地所有者應根據物種檔案的要求在一年内補種;第四,不實施可能導緻樹木過早枯死的行為;第五,澆水;第六,不濫用樹木所有權。這6項規定,還是對作為所有權客體的樹木的保護,實際上否定了樹木的主體資格。從瑞士的經驗來看,植物的尊嚴權屬于公法規定,如果我國的公法或私法承認植物的這一權利,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23條中作為知識産權之一的植物新品種權将受到沖擊。有人認為,植物新品種權是一種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産權形式。該權不是保護品種,而是保護大型植物育種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利益。通過這種方式,育種者被肯認為植物新品種的創造者,就像版權和專利被看作授予作者和發明家的榮譽一樣,育種者被授予植物新品種權。這意味着種植新品種植物(PVP)的農民被禁止出售他們從作物中收獲的種子,而且越來越多的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成員國禁止在非商業基礎上保存和交換種子。這也意味着農民每次購買種子都要支付特許權使用費。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從狹義和廣義上都否定了農民的權利。從狹義上講,農民自由保存收獲的種子的權利受到限制。從廣義上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不承認或支持社區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創新空間的固有權利。而按我國投贊成票通過的《聯合國農民和農村地區其他勞動者權利宣言》第5條(種子及傳統農法的權利)的規定:農民有權決定種植的種子品種;農民有權拒絕種植其認為在經濟、生态和文化上有危害的植物品種;農民有權拒絕工業化的農耕方式;……農民有權以個别或集體的方式選擇其生産的作物和品種,以及從事農、漁、牧相關活動的方式;……農民有權栽種并培育自己的品種,并有權交換、贈予或銷售這些種子。為了維護農民的此等權利,李昌平發表《給農民留幾粒真正的種子——緻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另外,植物新品種權可能與《生物多樣性公約》(1992年)第10條的這部分内容沖突:“每一締約國應盡可能并酌情:……(二)采取有關利用生物資源的措施,以避免或盡量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三)保護并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且符合保護或持續利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習慣使用方式……”植物新品種權構成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并不利于保護并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使用生物資源的方式。所以,如果植物的尊嚴權理論得到采用,植物新品種權的存廢将成為探讨的問題。
六
植物法律地位另類入憲與我國《憲法》中的植物條款的應有調整
如前所述,瑞士已完成植物法律地位入憲,還有一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植物法律地位入憲,我國為其中之一。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9條第2款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該規定課加國家保護珍貴動植物的義務,反言之,不珍貴的動植物得不到這樣的保護。盡管該款不講求平等,卻是我國動植物地位憲法化的初次嘗試,因為我國的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均無這樣的規定。此等規定之納入,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的影響有關。該聯盟1948年成立于法國,從1966年起,它開始出版瀕危物種的紅皮書和紅色名錄,以促進成員國對名錄中所列的物種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前文提及的埃皮凡諾娃等人的文章就提到了植物方面的俄羅斯本國紅皮書以及國際性的紅皮書,後一種紅皮書當出自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之手。該聯盟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在我國開展工作。受其影響,1982年7月,當時的國務院環保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組織召開了有關單位參加的中國植物紅皮書編寫會議,并正式成立編輯組。1982年12月4日,前引《憲法》第9條第2款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誕生。10年後的1992年,《中國植物紅皮書》第一冊正式出版,對何謂“珍貴植物”問題作出了部分解釋。這個“第一冊”列舉了388種植物,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保護植物143種,三類保護植物222種。說它是“部分解釋”,乃因為在筆者寫作本文的2023年10月,“第二冊”仍未出現。繼之,1999年8月4日,國務院批準了國家林業局和農業部發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該名錄共列植物419種,真菌3種,蟲草為其中之一。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略過省市級的和行業性(例如藥材業)的野生植物保護名錄不提。這些名錄使我國《憲法》第9條第2款關于植物的規定具體化。作為一個整體,它們的特征有:其一,從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自然資源的一種的角度規定植物,而非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規定;其二,隻關注野生植物和野生真菌,不關注農業植物以及其他高度卷入人類生産生活的植物和真菌,因為它們并不屬于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自然資源,也不珍稀;其三,隻關注列入名錄的植物免于滅絕,而不關注針對此等植物的基因操作。所以,我國《憲法》第9條第2款雖并非關于植物法律地位的綜合規定,但具有一定的民法意義。2003年的《烏克蘭民法典》第180條規定:“……3.紅皮書内列舉的動物隻有在法律規定的情形内并按法律規定的程序才能成為民事流轉的客體。”此款說的是紅皮書列舉的動物是限制流通物,類比過來,《中國植物紅皮書》等官方文件中列舉的植物也是限制流通物,不在紅皮書的名單中的植物可自由流通。
從1982年到2024年,時間過去了42年,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改變。其一,1992年瑞士修憲增加植物法律地位規定,它說明,人類對野生植物的滅絕的關注保持不變,但增加了對農業植物和其他“人化”植物蒙受魯莽的基因幹預的恐懼。其二,2000年《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條第3款采用植物非物的規定。其三,玻利維亞于2010年12月21日頒布了《地球母親權利法》,其第3條(地球母親)規定:地球母親是由所有生命系統和生物構成的不可分割的動态生命系統,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屬于同一命運共同體。此條未明言的植物和動物包含在“所有生命系統和生物”的一般表述中,它們是構成地球母親的要素。其四,智利2022年9月4日欲以一部生态憲法取代舊憲法,草案凡388條,其中98條直接或間接與環保有關。其第103條和第127條承認自然為權利主體。這個“自然”是“地球母親”的别樣表述,其中包括植物和動物。第148~150條設立了自然保護機構。該機構是自然這個主體的監護人。這一生态憲法草案盡管未通過全民公決,但它仍向我們揭示了當代憲法發展的生态方向。其五,也是最重要的,我國政府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從環境保護到生态維護的轉型,最好的例證是我國在已定每年的6月5日為全國環境日的前提下又定每年的8月15日為全國生态日,兩日同設表明設環境日不能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問題,必須設生态日“補火”。環境日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此等主義表現為把人之外的一切都當作客體,而生态日是生态中心主義的,此等主義的要旨是承認所有地球生命的主體地位,由此承認人類與其他地球生命的和諧共生。要指出的是,生态日的設立不過是一個小高潮而已。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報告就提出建設生态文明,這是一種超越工業文明的更高級的文明。2020年12月26日,我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其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長江流域生态環境保護和修複,促進資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制定本法。其第3條規定: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應當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長江保護應當堅持統籌協調、科學規劃、創新驅動、系統治理。兩個條文中的“保障生态安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是“生态文明”的體現。2022年12月30日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1條也有同樣體現:為了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态平衡,推進生态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制定本法。此條中的“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表述尤其具有生态性。
基于這些變化,我國《憲法》中的植物條款有了修訂的需要。建議在适當的時候修改之。首先,要把它改造成一個從環境保護出發的規定。目前筆者查到的規定植物法律地位的憲法共有6部,除《瑞士憲法》采取确立植物尊嚴權角度外,《巴西憲法》(1988)、《立陶宛憲法》(1992)、《阿塞拜疆憲法》(1995)、《玻利維亞憲法》(2009)、《吉爾吉斯斯坦憲法》(2010)都采取環境保護的角度。例如,《巴西憲法》第225條第7款這樣規定:保護動植物群,依法禁止一切危害動植物群的生态功能、導緻物種滅絕或者虐待動物的行為。又如,《立陶宛憲法》第54條這樣規定:“1.國家應當保護自然環境、野生動植物、自然個體和特殊價值地區,監督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及其恢複和增加;2.法律禁止破壞地球和地下土壤、污染水和空氣、對環境造成放射性影響以及破壞動植物群。”借鑒這些立法例,筆者建議把我國《憲法》的第9條第2款移到第26條的位置并在經一定修改後與其合并。其次,要把它改造成一個考慮全部植物(野生的和“人化”的)的規定和一個全面考慮植物的命運的規定,遭受滅絕誠然不幸,遭受基因篡改,變得不是它自己,盡管得以生存,也很難說是“幸”。按這樣的要求,我國《憲法》的第26條應如此行文:1.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态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2.國家保護動物和植物,禁止對它們實施任意的基因操作;3.國家組織和鼓勵植樹造林,保護林木。此條的第2款是第9條第2款的轉化形式。“轉化”一是表現為移位,這一移,意味着此條不僅保護國有的動植物,而且也保護集體所有和個人所有的動植物;二是表現為去掉了“珍貴”兩字,由此可包含非珍貴的野生植物和農業植物;三是表現為借鑒《瑞士憲法》第120條,增加了反任意的基因操作的規定。此款未明言植物是主體,但暗含植物具有基因自主權的意思,國家被設定為此等主體的監護人,但國家為抽象的存在,必須有具體的機關或個人實現國家的意志,檢察院為這樣的機關之一。到目前為止,我國檢察機關已提起保護珍稀植物的公益訴訟不少,證明此等機關可被考慮為植物主體的監護人。
七
結論
綜上所述,《阿塞拜疆民法典》首次從私法角度把植物去客體化,打破了非人類生命界的動物中心主義,其積極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但把所有的植物都去客體化有些過火,埃皮凡諾娃隻讓自由植物去客體化,而把為數有限的孤立植物保留在客體的範疇内,并對利用它們課加了限制。瑞士則從公法的角度規定植物的權利,尤其是其尊嚴權。兩種處理,殊途同歸,都達成了對植物法律地位的重設。
植物主體化是民事權利客體非生命化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動物主體化。如果把民法客體的去生物化看作一種趨勢,民法客體的去生物化的最後一步應指向真菌和微生物。《瑞士憲法》第120條提到了其他生物,應該指的是真菌和微生物。這可算作立法者以并非明示的方式考慮到了真菌和微生物的法律地位的立法例。我國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也不甘落後,把3種真菌列為保護對象。盡管動物和植物都是上述趨勢的作用對象,但兩者主體化的原因有異。動物之所以被主體化,乃因為它們與人結構類似,尤其在有大腦上類似,并且由于動物可借助聲音表達喜怒哀樂,人類比較了解動物。植物被主體化的原因則相反,在于我們不了解植物,由于它們與我們有太多差異,尤其是無腦,且不能用聲音表達,人類出于少知多畏的情懷賦予植物權利,以防止各種新生的生物技術的濫用。
植物有40多萬種,它們并非等同地受到法律的關注,樹木受到的關注最多,為它們誕生了兩個權利宣言,暫未看到其他植物赢得專項宣言的報道。所以,植物在法律的眼裡也有“貴族”和“平民”之分,樹木整體上處在貴族的地位,但在其内部,又有貴賤之分。例如,同屬于芸香科植物,枳通常被作為桔的砧木使用,代桔吸收養料水分,自己難見天日,套用前引《樹木權利宣言》第1條的表述,桔生活在大氣中,枳生活在地下。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所以,後者是前者的“奴隸”。人對兩種同科植物的關系的這種安排侵犯了枳的“尊嚴”,因為在此等情形,枳并非為自身而存在,而是直接為桔、間接為人類而存在。所以,植物主體化的落實,會導緻既有的一些植物彼此間關系的重整。
植物的主體化是民事主體“擴容”的一部分,被擴進來的有生物和非生物,後者如河流,被擴進來的理由是值得保護的利益。就被擴進來的生物而言,産生了尋找把它們擴進來的理由的問題。在單純以人為主體的情況下,主體的标準是理性的擁有。把動物擴進來的時候,找到的主體标準是感覺,對動物的新界定“有感生靈”隐含着這樣的标準。在動物的主體資格論證中,無人談論動物的智力問題。從本文可見,學界在論證植物的主體資格的時候,采用的标準是智力。所以,在非人類生命主體化的論證中,存在标準不一的問題。那麼,有無必要尋求統一的主體标準呢?如果有必要,可否把非人類生命的主體标準也界定為理性呢?因為智力是運用理性的條件,如果無腦的植物都有智力,有腦的動物更有。但是,理性不過是主體實施法律行為的條件,如果非人類生命盡管有理性(雖然這樣的理性低于人類的理性),但不能自行實施法律行為,這樣的理性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在确定非人類生命的主體資格時,我們還是堅持匈牙利學者亞曆山大·内卡姆(Alexander Nékám,1905—1982)的利益說為好。斯人著有《法律實體的人格的概念》,主張以“法律實體”的概念取代自然人(person)、法人(corporate person)、權利主體(subject of rights)的概念。内卡姆反對自然人概念的原因是它被用來指稱人類。反對法人概念的原因是該概念是對自然人的概念的攀比。而法律實體是一個被動的、抽象的、人為的概念,除了與抽象的法律權利相關外,沒有任何意義。按照這一理論,隻要是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載體,無論它是否有生命,以何種方式存在,都是法律實體,從而享有人格。實際上,自然主體化最重要的主張者克裡斯托弗·斯通也是這麼想的,其劃時代論文的題目就是《樹應該有訴訟資格嗎?邁向自然物的法律權利》,這個題目表明作者主張樹是訴訟主體的立場,但斯通并未對樹具有智力提出論證,因為這是不必要的,樹是生态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夠了。所以,斯通之後的許多學者提出的植物具有智力的論證,不過是在主體資格賦予上拟人的餘迹,或反對動物中心主義而已,可看作冗餘的論證。總之,非人類生命體的生存,是值得保護的利益,如同自然的健全維持是值得保護的利益。所以,有理性的非人類生命和無理性的自然的主體化理由實際上是一樣的。然而,盡管非人類生命進入主體範疇的過程就是去人類中心主義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還是發現,人類确實在各個方面(尤其在頭腦方面)都居于優越的地位,但此等地位切不可濫用,而應用在照管非人類生命主體和自然上。
接下來要講到的是有害植物是否要像其他植物一樣取得主體資格的問題。暫未看到關于有害植物主體資格的讨論,但看到了關于是否要消滅有害動物蚊子的讨論,結論是蚊子有清除廢物、傳播花粉、作為魚類的食物等積極作用,不可完全消滅。可以把對蚊子的這些肯認移用于所謂的有害植物,它們的積極功能也許我們隻是暫未看到,但我們應相信“每物必有其用”的箴言。
最後回答本文标題提出的問題:植物是什麼?答曰應該是主體。或問,為何非要把動物和植物主體化,把它們當作特殊的客體不行嗎?斯通在其劃時代論文中考慮了這一問題,答案是把包括動植物在内的自然物主體化的原因是避免它們被其所有人出賣。例如,我的土地被你污染,你給我很好的賠償,我滿意之并遷居他地,而犧牲了我原來土地上因為污染被殺死的動植物。相反,把動植物作為主體,侵權人不僅要賠償我,而且要恢複它們。斯通舉了這樣的例子,假設一個海膽群落被毀,如果在此等群落的原來栖居地恢複它們不可能,則要在地球上的其他某個地方重建一個海膽群落。當然,擺脫植物不過是特殊客體的推理的有力安排是讓植物也承擔責任,斯通未直接考慮過這一問題,但考慮了包羅更廣泛的自然物的此等問題。他問:河流侵權了怎麼辦?河流淹死人,不停泛濫并且毀壞莊稼,或者森林燃燒,向鄰近的社區縱火怎麼辦?如果建立了信托基金(通過讓自然物累積他人侵害它的損害賠償金作為自己的損害賠償金),就可以利用它們來滿足針對自己的不利判決,使自然物承擔其對其他權利持有者所造成的某些危害的成本。此論可套用于植物。按照我國《民法典》第1234條和第1235條的規定,侵害生态環境者要承擔生态修複費用。被侵害者是植物的情形,此等費用在完成修複後有剩餘的,可成為上述信托基金的來源。人類利用植物獲得的利益,也可拿出一部分投入此等基金,當植物(例如森林)自燃緻人損害時,此等基金可用來賠償受害人。所幸的是,植物由于其不動性,緻人損害的可能性比動物和河流不知小多少,所以,上述基金的存在必要性很小。當然,上述安排看起來粗糙,但哪個新事物誕生時不是粗糙的呢?每個新事物都是在實踐中改進自己并達至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