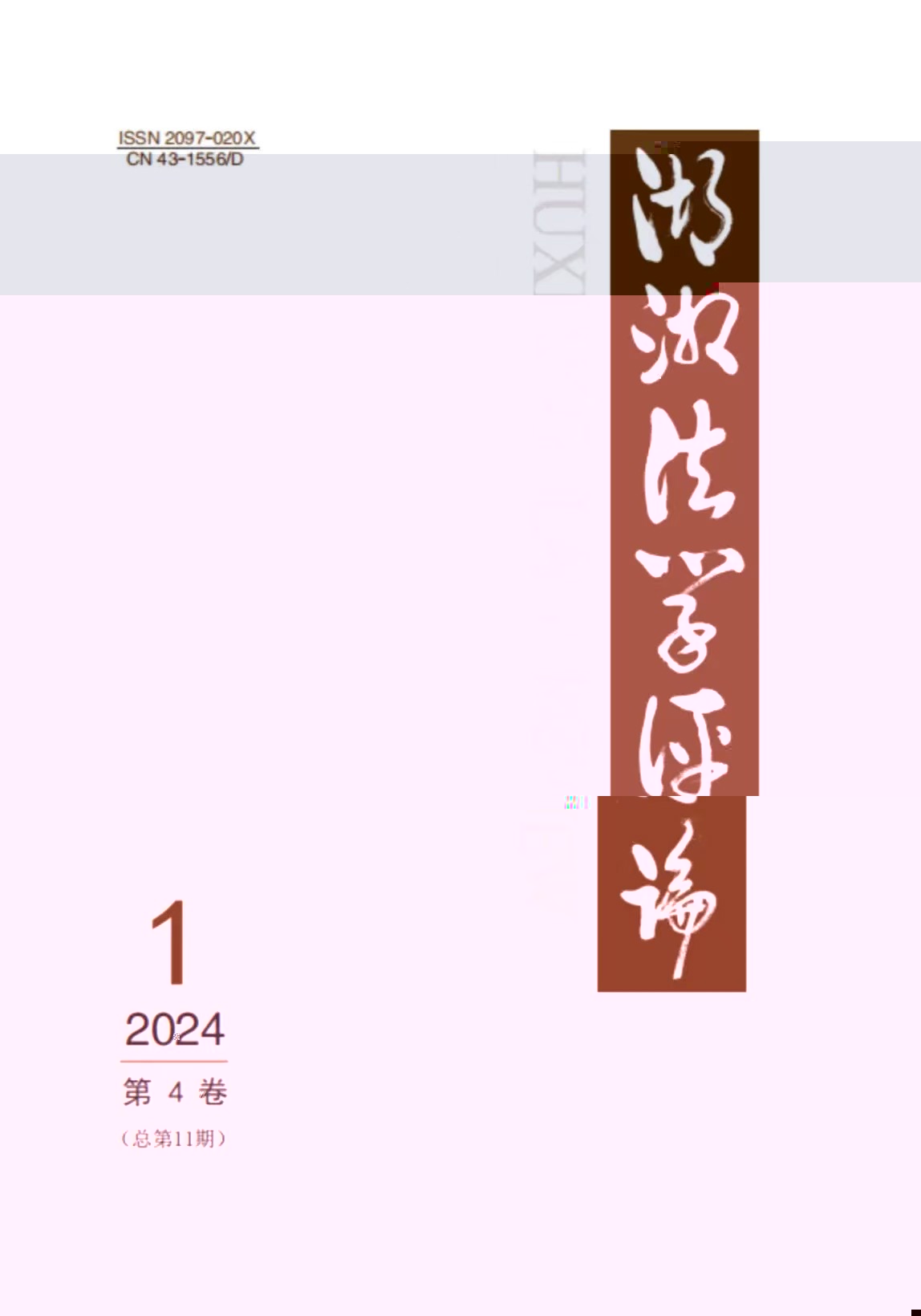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4年第1期(總第11期)“專題筆談”欄目
【作者】陳禹橦,法學博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二)》新增了三類關于民營企業人員的特殊背信犯罪,旨在從立法上進一步落實對民營經濟的平等保護要求。要注意實質性地理解平等保護要求,從侵害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利益行為的實質特征出發,通過構成要件的“增減調整”,真正落實平等保護要求。在具體适用新增罪名時,要注意《刑法》與新修訂的《公司法》中關于忠實義務等規定的有效銜接,在法秩序統一性原理下确保刑事違法性的獨立判斷。根據刑法解釋并參考指導性案例,《刑法》第165條、第166條、第169條新增第2款應對第1款法定刑“全部援引”。
【關鍵詞】特殊背信犯罪;平等保護;法定刑援引;忠實義務
2023年12月29日通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165條、第166條、第169條中增設了三類關于民營企業人員的特殊背信犯罪,旨在進一步加大民營企業權益平等保護力度。徒法不足以自行,隻有将目光不斷往返于社會生活事實與刑法條文之間,才能準确、實質地把握立法修訂的精神,真正落實立法修訂的目的。因此,本文拟立足司法實務,從立法背景、解釋進路方面,對新增特殊背信犯罪條款的理解與适用進行探讨。
一
立法背景——
落實民營經濟的刑法平等保護要求
理解新增特殊背信犯罪條款的立法背景時,要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民營經濟平等保護的現實需求
随着社會的發展變化,當新的法益侵害不斷出現,原本輕微的法益侵害演變為嚴重的法益侵害時,刑法立法上就需要增設新的犯罪予以應對。近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迅速。據統計,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内生産總值、70%以上的高新技術企業占比、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貢獻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過去針對國有企業規定的一些背信腐敗犯罪在民營企業開始出現并增長,尤其是對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等行為反映比較突出,這些行為給企業造成重大損害。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加強民營企業産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23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作了新的部署,對民營企業内部腐敗的防範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2013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的涉及這方面的議案、建議和提案就有60多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大對民營企業财産保護力度,落實對民營經濟的刑法平等保護,成為刑事法治責無旁貸的事情。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二)》将部分具有社會危害性、具有刑事規制必要性的侵犯民營企業利益的背信行為納入調整範圍,與時俱進地完善了刑法侵害民營企業的罪名體系,适應保護民營企業的實踐需要,符合法益變動性對于刑事立法的指導價值。
(二)民營經濟平等保護的立法進路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到《刑法修正案(十二)》,體現出不斷加大民營企業權益平等保護力度的立法進路。在立法特色上,要注意理解立法修改的漸進思路和立法範圍的謹慎劃定。
1.立法修改的漸進思路
對我國刑事立法在民營企業保護上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保護範圍不夠、保護力度不足等方面。2020年12月26日通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僅對後者作出了回應,亦即對有關涉企犯罪作了修改完善,進一步提高和調整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資金罪等民營企業有關商業腐敗犯罪的刑罰配置,除不判處死刑以外,民營企業人員腐敗犯罪與公職人員腐敗犯罪的刑罰已經基本接近,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刑法對民營企業保護力度不足的問題。雖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訂的過程中,曾有意見提出增加民營企業渎職罪名,但考慮到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總體還處于不平衡階段,很多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日常管理不規範,規定渎職類犯罪,界限不好把握,可能造成刑事司法力量過度介入民營企業生産經營的問題,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未作出保護範圍的變更。《刑法修正案(十二)》将國有企業渎職罪名中的第165、166、169條三個罪名擴展到民營企業,體現了立法修改的漸進性。
2.立法範圍的謹慎劃定
不少有力的觀點主張,應當增加對應國有企業渎職全部罪名的民營企業渎職罪名,但《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時,隻是将民營企業内部人員發生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或出售(國有)資産三類“損企肥私”的背信損害企業利益行為規定為犯罪,體現了立法上對于民營企業背信行為刑事規制範圍的謹慎劃定。同時,立法機關工作人員在解讀《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時反複強調,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還不平衡、情況也比較複雜,要求司法機關在案件處理上要充分考慮企業實際情況,特别是對于涉及企業内部股東之間的矛盾糾紛,注意把握好犯罪界限和民刑交叉法律問題,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幹涉企業正常生産經營活動。這也是理解本次修法在“加大對民營企業保護力度”與“避免打擊範圍過大”之間平衡考量立法意圖的關鍵。
(三)民營經濟平等保護的實質理解
刑法學界一直有觀點呼籲取消犯罪主體的差别待遇,落實刑法對民營經濟的平等保護。但對于何謂刑法的平等保護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将犯罪主體擴大至民營企業對應人員,實現國有單位人員與非國有單位人員渎職行為的對稱性入罪,相應的民營企業人員渎職罪構成要件行為、刑罰後果均應完全相同。但也有觀點認為,需要确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的公平法律觀,要關注不同主體及其行為的差異性,追求實質公平的價值目标;考慮到憲法上公有制、非公有制經濟重要性程度的不同,以及當前不同所有制主體治理結構上的差異,不能簡單地将涉及兩種不同所有制的犯罪“拉平”,否則反倒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本文認為,要落實刑法對民營經濟的平等保護,就必須将侵害民營企業财産的危害行為作為犯罪處理,從而有效地禁止這種行為,克服刑法保護不公平的實質缺陷。但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的内部治理結構還有待完善、法治理念還有待提升的現實條件下,應當從侵害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利益行為的實質特征出發,通過構成要件的“增減調整”,真正落實平等保護要求。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為例,之前公布的草案在第165、166、169條分别增設第2款,将現行對“國有公司、企業”等相關人員适用的犯罪擴展到民營企業,并未修改其他構成要件,似乎實現了平等保護,但這種忽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不同經營特點、人員組成的做法可能帶來實質不平等的後果。例如,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擴展到民營企業後,如果采用完全相同的構成要件,可能忽略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廉潔從嚴的不同要求,也不符合民營企業中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的本質特征,導緻犯罪門檻過低。因此,最終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在擴大本罪主體範圍之外,增加了“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緻使公司、企業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其他構成要件。
二
解釋進路——
民營企業内特定背信行為的入罪
立法層面解決了特定民營企業内部人員故意背信損害企業利益行為的入罪問題,司法層面需要重點考慮的,就是新增罪名的解釋适用問題。至少有以下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特定背信犯罪解釋的基本思路
在立法活性化的時代,刑法與前置法都處在不斷修訂變化中,尤其要關注動态變化中的法法銜接問題。本次修法除《刑法》第165條犯罪主體由“董事、經理”統一變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體現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修訂内容的銜接外,并未對2023年12月29日通過的新《公司法》進行更多的“立法銜接”嘗試。本文認為,在《刑法》與《公司法》司法适用銜接的過程中,應當堅持刑事違法性獨立判斷立場,關注《公司法》等法律規定變化,立足公司自治特征與運營方式等對刑法相關條款進行解釋适用,準确劃定相應犯罪圈。
1.“入罪銜接”中堅持刑事違法性獨立判斷立場
《刑法》第165、166、169條主要涉及民營企業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董監高”)及其他工作人員的背信犯罪,在适用相關條文時應當關注《公司法》對這類人員義務規定的變化。例如,新《公司法》第八章完善了“董監高”忠實義務及勤勉義務的規則體系,其中第180條首次在法律規範層面對兩種義務類型的内涵作出定義,忠實義務是指“應當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沖突,不得利用職權牟取不正當利益”,勤勉義務是指“執行職務應當為公司的最大利益盡到管理者通常應有的合理注意”。新《公司法》除了延續舊法第181條列舉的違反忠實義務行為類型外,還細化了“自我交易”“謀取公司商業機會”“同業競争”等特定行為的處理規則。
但是,在充分關注上述《公司法》規定内容的基礎上,基于不同部門法立法目的的差異性,仍然要堅持刑事違法性的獨立判斷立場。例如,《刑法》第165條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可能涉及“謀取公司商業機會”“同業競争”行為,在解釋“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時,必須注意不同法律立法目的對解釋的影響。我國《公司法》基于規制情形和規制功能的互補性對公司商業機會原則、競業禁止義務采取了二元體系,但二者存在交叉重合。從刑事構成要件實質認定角度出發,認定本罪“同類的營業”範圍時,既要包括公司章程記載的經營範圍、公司的實際經營活動,也應包括與公司有實質性利益沖突的經營活動,避免處罰漏洞。再如,《刑法》第166條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可能涉及“自我交易”“關聯交易”行為,法條規定的本罪主體是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而未限制為“董監高”,這是因為法條明确列舉的盈利業務自我交易,高價采購低價銷售,采購、接受不合格産品、服務三類具體行為,和“使國家利益或公司企業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後果,決定了本罪的處罰對象針對的是嚴重侵犯公司、企業财産權益的行為,範圍大于《公司法》規定的忠實義務,在這一背景下,解釋“親友”“盈利業務”“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等構成要件要素時,不宜過于限縮。此外,《刑法》第169條徇私舞弊低價折股或出售公司、企業資産罪的主體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範圍不限于董監高,也是基于本罪行為顯然是違背忠實義務嚴重侵害公司、企業的财産權益的行為,在認定犯罪主體時,可以适當放寬條件。
2.“出罪銜接”中堅持刑事違法性獨立判斷立場
相比之前公布的草案,最終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二)》第165、166條第2款,在“實施前款行為”前均增加了“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要求,這也使得新增罪名具有了狹義上的“行政犯”色彩。一方面,這一規定銜接了刑法與前置法,指示司法人員适用罪名時,應找到違反的《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另一方面,該規定也在提示司法人員一定要注意《公司法》上相應禁止條款的例外規定或者說抗辯事由,可能成為刑法上的出罪事由。
根據法秩序統一原理,前置法中合法的行為,雖然沒有在刑法中明文規定為違法、責任阻卻事由,但從犯罪構成要件的實質解釋來看,不能被認定為刑事違法行為。例如,在解釋适用親友非法牟利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時,就必須考慮修訂後的《公司法》第183條、第184條規定的謀取商業機會、競業禁止的豁免情形,不能将《公司法》上的合法行為評價為犯罪行為。值得注意,實踐中不少民營企業的運營、決議程序往往并不規範,行為人作為涉案民營企業實際控制人、經營者,未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同意實施同業競争、關聯交易、自我交易等行為的,也要實質判斷是否符合罪名的本質特征和保護法益,是否損害民營企業利益等,避免過度介入股東糾紛等公司内部治理問題,造成刑事打擊範圍失當。
(二)“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的法定刑援引問題
我國刑法分則“罪狀+法定刑”的立法模式決定了在性質相近、危害相當罪名的法條中,基本采用援引法定刑的立法技術,這容易引起如何理解援引法定刑的争議。本次修法新增的《刑法》第165、166、169條第2款中,均有“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的表述,而第165、166、169條第1款中均有兩檔法定刑,極易産生的争議便是:第2款援引法定刑的情形,究竟是對第1款法定刑的全部援引還是部分援引。
這一法定刑援引争議在被兩高分别作為指導性案例收錄的“馬樂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中,體現得極為明顯。該案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了“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未規定“情節特别嚴重”情形,因此,隻能援引《刑法》第180條第1款“情節嚴重”的法定刑對馬樂量刑。但一、二審檢察機關以及提出審判監督抗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均認為,《刑法》第180條第4款援引的法定刑情形包括第1款處罰的全部規定,包含“情節特别嚴重”情形,因此,可以援引《刑法》第180條第1款“情節特别嚴重”的法定刑。
本文認為,《刑法》第165、166、169條新增的第2款罪名,可以援引第1款的兩檔法定刑。以修訂後的《刑法》第165條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例,其他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實施前款行為,緻使公司、企業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如果“獲取非法利益”“數額特别巨大的”,應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理由是:第一,從文義解釋看,“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可以解釋為對第1款定罪量刑規定内容的全部“依照”,自然也可以包括第1款規定的第二檔法定刑情節。第二,從立法目的解釋看,《刑法修正案(十二)》将三類常見的“損公肥私”背信損害民營企業利益的行為入罪,系認為上述行為的危害性已經達到了刑事處罰的程度,在第165、166、169條新增第2款罪名,是為了解決刑法平等保護的問題,在增加部分罪狀的情況下,得出“全部援引第一款法定刑”的結論,符合本次立法目的和罪責刑相适應原則要求,也為懲治更為嚴重的行為保留了“法定刑升檔”的空間,未來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具體規定第2款法定刑升檔條件。第三,從立法技術看,《刑法》第141條第2款生産、銷售、提供假藥罪,第164條第2款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303條第3款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等多個條文中均有此類規定,一般也都參考“馬樂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指導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明确“第一款法定刑全部援引”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