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2年第3期“傳統文化與法治”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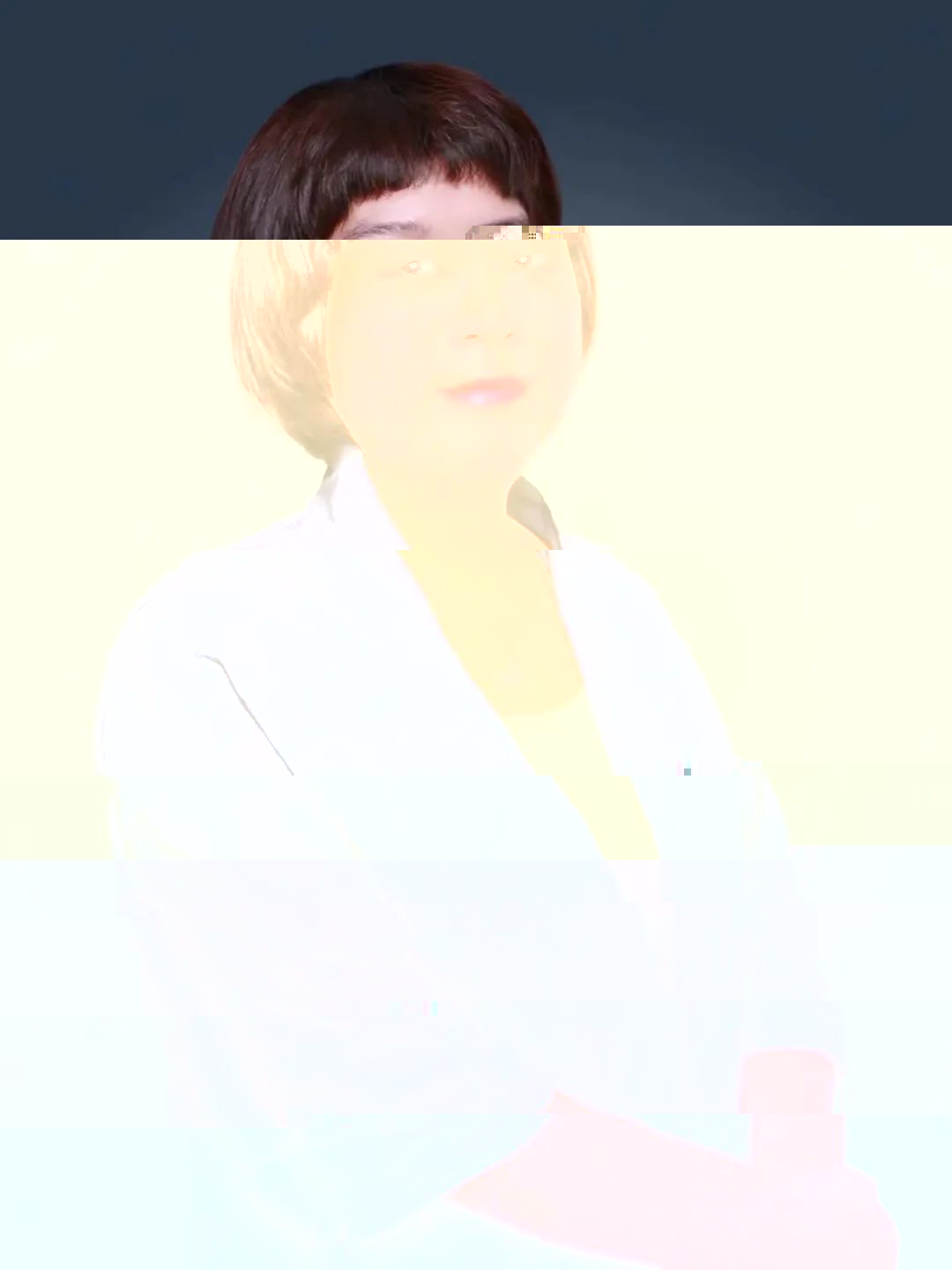
【作者】段曉彥,法學博士,福州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教授;宋鵬,福州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碩士。
【摘要】為了解決民初司法審判無法可依的困境,大理院以條理的名義引入法律學說作為法律淵源的重要補充。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域外民事立法對學說的肯定、本土成文法的缺位以及中譯日本學者的理論為大理院在民事裁判中适用學說提供了契機。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既有着微觀上對法律概念、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的闡釋,也有着宏觀上對法律思想和價值的論述。大理院在适用法律學說的過程中區分了作為裁判理由與裁判依據的學說,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以确保裁判的權威性與正當性,在傳播先進的民法理論的同時兼顧了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法律學說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運用,對其後的民事立法與司法産生了深遠影響,更為中國百餘年的民法現代化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關鍵詞】法律學說;法律淵源;大理院;條理;判例
一.問題的提出
在法律發展的早期,法律學說對于司法裁判而言具有重要地位。“學說,即個人關于法律問題的見解,在法律不完備時代,常采取名家的學說作為法律的直接淵源。”例如古羅馬時期,享有特權的法學家針對具體案件的答疑被明确承認為法的淵源,具有法律的約束力,這一特權還進一步延伸到他們的著作當中。同樣在古代中國,由西漢董仲舒所提倡的“《春秋》決獄”使得儒家經典中的教義學說取得了正式法律淵源的地位,其效力在某些案件中甚至可以越居法律之上。探其原委,“從法制史的發展來看,引經斷獄的源起,一在補充法律條文的不足,一在解決與情理的龃龉;蓋科條有限,情僞無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日頒布的《關于加強和規範裁判文書釋說法理的指導意見》中第13條規定,法官在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之外可以運用“法理和通行學術觀點”論證裁判理由。這一規定的出台,肯定了學說對于司法裁判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學者們對于法律學說司法适用的關注。圍繞這一主題,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法律學說法源地位的探讨,對司法裁判援引法律學說的運用實态、理論建構及功能意義等方面。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從理論與實務的角度基于當代司法現狀對法律學說的适用進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缺乏對于近代中國司法曆史的觀照。在民初無民法典的特殊情況下,學說作為條理之一已被當時的司法實踐所采納,這是學說在中華司法曆史中被适用的重要節點。概覽學界對民初大理院與這一主題的相關研究,也均是淺略涉及而并未細緻展開。
民國初期,舊法難以為繼、新法如日方升,法典的空白和新舊法律文化的沖突為法律學說的司法适用提供了重要機遇。法律學說亦不負所托,依附于條理作為補充性的法源為解決當時“無民法典如何進行民事審判”的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則以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案例為基礎,聚焦于法律學說的司法适用實态,借此厘清大理院運用法律學說的方法與特點及其對後世民事立法與司法所帶來的影響與意義。
二.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契機
(一)域外經驗
近代歐陸各國在民事立法的過程中,多認可法理之類的抽象法律概念具有兜底性的法源地位。日本早在明治八年(1875)六月八日,《太政官布告》第 103 号“裁判事務心得”第 3 條中指出:“于民事裁判,無成文法者,依習慣;無習慣者,推考條理而判斷之。”實際上,日本的“法律适用規則”源自對法國、奧地利和德國法的綜合借鑒。例如 1812 年《奧地利普通民法典》中的“民法的基本法則”第 7 條規定,無法可依時“以自然法的法律原則對案件作出裁判”。此後,1888 年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第 1 條規定:“法律無規定之事項,準用關于類似事項之規定。無類似事項之規定時,适用有法規精神所生之原則。”《德國民法典》的理由書中明确指出:“在缺少立法措施之場合,以法學為法。”1907 年的《瑞士民法》第 1 條直接肯定了學說的法源地位:“凡在本律文字,或精神以内之事件,均受本律之支配;如審判官裁判時無可适用之律文,應依習慣法;如無習慣法,應依如審判官自為立法者時所預定之規則,惟應斟酌于學說及法理。”其實,“條理”“法理”“自然法的法律原則”以及“法規精神所生之原則”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作為一種兜底性的法律淵源其内涵具有内在的一緻性——一種理性的法律思考,也正是因為這類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存在,才為法律學說的司法适用提供了空間。
受立法的影響,以上各國在司法實踐中常會援引學說。特别是在德國,受法教義學的影響頗巨,法學理論與司法實務之間聯系緊密、互動頻繁。法官們在司法裁判中“較之判例,更熱衷于頻繁引用學說,并撰寫内容可與學術論文相媲美的判決書。”在日本,學說亦是重要的法律淵源。楊仁壽先生曾談及日本實務中常引德國等國的學說以及大學教授的法律見解為裁判依據。并且學說的地位随着法律的發展而日益重要,例如在近代法國,學說一度被排除在法源之外,但到現代又重新成為重要的裁判理由。
大理院的法官們多數具有留學背景,其中又以德日瑞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主。得益于此,他們對域外關于司法裁判援引學說的情況并不陌生,也因之能潛意識地運用到本土實踐之中。
(二)本土境遇
民初之際,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法條寥寥無幾,遠不足以支撐大量民事案件對裁判規範的需求,這為大理院适用學說提供了前提。同時,晚清的民事立法對學說理論的采納也為大理院适用學說提供了寶貴經驗。
1. 既有規範存在不足
民國初年,除了繼續延用前清的《大清現行刑律》以及當時頒布的零散的民事特别法令外,尚無一部成文民法典可供司法裁判參考。然民事案件不能以無法可依為由而拒絕審判,大理院于是效仿前述日本明治八年《太政官布告》第 103 号裁判事務心得,在 2 年上字第 64 号判例中确立了彼時法源之順序:“判斷民事案件應先依法律所規定,無法律明文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則依條理,蓋通例也。現在民國民法典尚未頒行,前清現行律關于民事各規定繼續有效,自應根據以為判斷。”
然而,這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前兩位的法源在實踐中運用面臨重重困難。作為第一位法源的“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既無明确的内容範圍,又帶有難以分離的刑事制裁性規範,其法律精神以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為基礎而與社會發展趨勢相悖。作為第二位法源的習慣亦面臨窘境。一方面中國地廣人稠、習慣頗多,調查與整理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各地習慣不一,許多習慣因其地域性的限制無法獲得普遍的适用。即便确為某一地區通行之習慣,也常會因為與交易安全、社會安甯、善良風俗等現代法精神相悖而被排除适用。相較之下,條理的範圍相當廣泛,具體内容可以由大理院推事們依據具體案情而靈活适用。于是,作為第三位法源的條理雖居末位,卻因意涵豐富而适用最廣,而學說恰是條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2.晚清民事立法提供經驗
大理院之所以将學說作為條理内容之一适用于裁判之中,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晚清民初立法活動的影響。古來各國編纂法典無一例外的都要參考法律學說,“夫直接以學說為法律事雖危險,然學者之解釋法律或批評法律實是将來制定法律之材料”。《大清民律草案》亦是如此,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原本後出最精之法理”:“學說之精進,由于學說者半,由于經驗者半,推之法律亦何莫不然,以故各國法律愈後出者,最為世人矚目,義取規随,自殊剽襲,良以學問乃世界所公,并非一國所獨也。”《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謹遵這一原則,法條下的立法理由中常可見其背後所參考的學說。例如《大清民律草案》第 1028 條規定:“以所有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産者,即取得所有權。”其立法理由中說到:“無主物因先占而取得所有權之制度,自古各國皆有之。其主義分為自由先占主義,及先占權主義。自由先占主義者,使先占有者,自由取得無主物所有權之謂。先占權主義者,非有先占權之人,不得因先占而取得無主物所有權之謂。本案既于不動産認先占權主義,故複設本條,于動産認自由先占主義,使先占無主動産者,得以其動産為其所有,而利用其動産也。”即便在立法理由中不展現具體學說,也常以“古來學說聚訟”一語表明立法對于學說的借鑒。
《大清民律草案》同學說一樣,均通過條理被适用于大理院的司法裁判之中。通常情況下,大理院會優先适用《大清民律草案》的内容,但在《大清民律草案》無規定或已有規定不合适之時,推事們或許會直接尋找學說進行裁判。對于“司法兼營立法”的大理院來說,在司法審判中所運用的法律學說可以理解為一種超越立法階段的“準法”。
(三)理論支撐
近代中國法學的發展伴随着西方武力入侵後的文化輸入,其中法學基礎理論就主要通過中譯日本學說的形式對中國産生影響。當時介紹這一學科的書籍也主要是譯自奧田義人、梅謙次郎、織田萬等日本學者所著的法學通論,這其中即有對法律淵源以及法律學說的介紹。
日本學者奧田義人從立法的角度認可法律學說的法源地位,他認為“蓋法律之進步,每後于社會之進步。社會而已進步也,則事物愈多,需要愈增,法律即有不完全之勢。其使之因應社會之情狀而改正之增加之者,厥惟學說。是以學說為法律之淵源也。”但就學說本身而言,“其無法律之效力,固無論矣”。此外,他進一步介紹了學說獲得法律效力的四種方式:以法學者法律解釋權;與學說以法律之效力;編纂學說而為法典;學說養成習慣法。
在矶谷幸次郎所著的《法學通論》一書中,他認為法律淵源是指“法律之起源”,即“法律以何者為材料”。而學說的法源地位,從立法的角度來看,“近世立法者,凡欲編成文法,無不參照學者之意見,實法律淵源中重要之部類也”。然從司法的角度看,“法學者之學說,出一人之私見,無法律之效力固不待言”,但是裁判官與律師可以參考學說對法律進行解釋。
織田萬也持有類似觀點,他認為法律淵源即“所以構成法律規則之材料”,學說隻可供立法及裁判所參考,而不能如古羅馬那般直接付以法律效力。并且他還進一步解釋了學說在古時被賦予法律效力的原因:“蓋古時立法機關其組織未臻完備,故于學者之說,每直接附與法律之效力。至近世社會進步,學說之于法律,雖或有間接之效力,然其成為不成文法之基礎者,則固未有也。”
民國學者方剛綜合日本學者梅謙次郎與大石定吉的學說著有《法政提要》一書,其中亦指出學說本身固無法律效力,然而從構成法律之材料的角度來看,學說作為法律淵源已由法制史多次證明, “如日本民法多系其編纂委員之博士所有之學說”。
縱觀當時譯自日本的一系列《法學通論》著作,均站在立法的角度肯定學說是一種法律淵源,但同時也否定學說本身具備直接的法律效力。受這一影響,當時學者們對法律淵源的認識主要系指 “構成法律規則的材料”,這種法律淵源觀是站在立法的立場表明法律是如何産生的。随着法律體系的完善,法律淵源的語義也逐漸從立法立場轉換到司法立場,法律淵源更多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規範存在于何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民初大理院審判法源的問題需要站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進行。民國初期,中國的法制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法律體系猶如古羅馬早期之際極不健全。因此,立法立場的法律淵源觀恰恰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正如織田萬所指出的,學說直接獲得法律效力正是因為立法機關不完備緻使法律過于疏漏所導緻的。學說作為立法的重要材料,在民初那樣法制窘迫的條件下,無成文民法可參考的推事們在司法中直接引用甚至是創造學說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實态
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主要目的是彌補民事法律的空白并借以豐富民法理論。這一過程,從具體的法律概念、法律規則到抽象的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均有涉及。在考察大理院于民事裁判中對法律學說的适用實态之前,需要說明的是,法律學說與外國立法例、一般法律原則以及法理之間存在一定重合或交叉的部分。就法律學說與外國立法例而言,大理院援引的學說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國外法學界,其中很多已是得到國外立法認可的民事理論,但由于外國法律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國,因此我們将外國立法例背後的學說作為大理院援用的實質對象加以考察。法律學說與一般法律原則、法理的關系從形式上講是具體與抽象的關系,所以,我們将法官運用所學對法律原則以及法理等抽象的法概念進行具體化并創造出的法律規則也視為法律學說。之所以将法官創造的規則視為學說的一種,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因為傳統中華法系瓦解後的十幾年間,民國法制建設仍處于探索階段,雖然這一過程以移植大陸法系的法制為主,但判例也在司法中具有實際的約束力,我們不能斷然稱之為大陸法系抑或普通法系。況且“通說認為法官法不是法律淵源”,因此法官造法不能等同于直接創造出有拘束力的法律規則。二是通過對案例的整理發現,存在法官适用學說而導緻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甚至出現完全相反的裁判觀點,因此從法的安定性與可預測性的角度,也不宜将其直接認定為法律規則,相反,歸入學說更為恰當。
誠然,囿于法律紛繁複雜,學說亦是數不勝數,本文重點不在于對每個學說進行追本溯源的考證,而是側重于大理院适用學說的實态與方法。
(一)闡釋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作為最基本的法律元素,明确其含義是适用法律規則的重要前提。伴随着法制的近代化以及西方法律思想的輸入,衆多法律概念湧入社會。在法學教育尚不普及的民初社會,解釋法律概念的任務便交由大理院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實現,這一過程有時就需要借助學說予以論證。
例如民法中“善意”一詞的含義,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1248 号判例稱:“蓋法律所稱善意,即不知情之别稱,并非善良意思或好意之意,故曰善意占有者,即确信其占有之物為自己所有,而于他人所有為不知情之謂也,此理甚明。我國法文未備,即參考外國法文及學說,當然無可疑議。”民法中的“善意”起源于羅馬法,包括“訴訟上的善意”與“取得時效制度中的善意”,在後者中“善意”是一種主觀認知,即認為自己行為正當的意思。“善意”的概念并無太多的理論深度,“善意占有”的含義也是法學界不言自明的通說。本案中,被上告人以房契作押向上告人借款,後雙方因庚子兵變逃難于外。事息後,上告人先歸來且為确保抵押物免遭損毀而基于好意對被上告人的房屋進行管理并享有收益。因此,上告人主張善意占有被上告人的房屋,取得所有權。法官則參考國外立法與法學通學說點明“善意”并非善良好意,而是不知情的意思,“善意占有”即要求占有者不知其占有物為他人所有,而本案中上告人顯然清楚自己占有他人房屋但卻誤解了“善意”在法律中的含義,因此無法主張善意占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權。
再比如意思表示中“強迫”這一概念,大理院于 4 年上字第 1739 号判例中認為:“所謂強迫,應與所表示之意思有因果聯絡,即因他人表示有将加不利之威脅,因而生畏怖心,不得不表示其意思者而後可,如果威脅行為由行使權利人以正當方法行之則不在強迫之列。反是,行使權利人若威脅義務人實出過當,或則不法,或與善良風俗不免違反之時,自應以有應準取消之強迫論。”本案中,上告人主張自己與被上告人之間簽押的還款合同系由被上告人強迫不得已為之,上告人所承擔之債務應由各股東分别按股份償還而非由自己完全承擔。大理院認為,因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當準許撤銷,唯強迫認定的标準尚無明文規定。于是法官根據通行學術觀點,認為法律上的強迫應滿足兩個标準,一則強迫須以不法的方式為之,二則強迫須達到使表意人喪失意思表示自由的程度,而不能僅從字面或經驗上進行理解。本案中,原審法院對強迫一情節認定不清,大理院則通過借鑒學說澄清了強迫的法律意義,并為原審法院重審時認定當事人雙方簽訂合同是否存在強迫的情節提供了判斷标準。
(二)尋譯法律規則
“學說,是研究法學者,所下之法理上之見解也。法律條文之不備,立法者取其間接圖以補充;法律條文不明,司法者取其見解以供參考。”學說的功能一在于補充法律條文之不足,促進立法的完善,一在于解釋法律疑惑之處,幫助法官在審判時正确适用法律條文。民初大理院審判之際,不僅有參考學說釋明法律條文之舉,亦會直接引用學說作為規則,填補法律漏洞。
通常情況下,法律規則适用遇有不明之處時,法官便會借用學說予以解釋。在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316 号判例中,上告人與被上告人原共同經營典當行,共持股份、共享債權。兩人分家後,上告人主張适用債權債務抵銷規則以所持股本與債權券與被上告人之債權相互抵銷。法官則首先就抵銷權構成要件分析道:“債權抵銷之要件有四:(一)當事人須互負同種标的之債務;(二)雙方之債務須均已至清償期;(三)須依債務性質及法律準許其抵消;(四)須當事人未預表示反對之意思。以上要件有一不備,不得主張抵銷。”繼而認為,上告人所持股權與被上告人所有債權非同一種類,不得抵銷;唯上告人寄存于被上告人處的債券若已由被上告人行使債權而受有給付,方得主張抵銷。不止于此,在 7 年上字第 500 判例中,大理院又對何謂“同種類之标的”與“當事人未預表示反對之意思”的内涵進行了學理解釋:“抵銷債務之要件,所謂雙方債務須有同一種類之标的者,系指為債權标的之給付須系同一種類而言,非謂債務之原因亦須同一;又所謂須當事人未曾表示反對之意思者,系指當事人于主張抵銷以前,未經約定其債務不須抵銷而言,非謂抵銷須兩造之合意。”大理院在以上判決中對抵銷權構成要件及其構成要件的内涵進行了深層次理論闡釋,确保了債權債務抵銷規則能夠正确适用于案件糾紛的解決。
獨特的是,民初之際法律學說的功能不僅在于解釋法律規則,亦可以直接填補規則空白。在大理院 3 年上字 803 号判例中,被上告人捷成德資銀行因上告人不履行到期交貨義務請求賠償損失。此類涉外案件首要問題是尋求準據法,而民初之際又無國際私法可參考,法官則查閱學說認為:“凡審判寄居内國之外國人民相互間,或與内國人民間所生之民事訴,應适用何地之法律,因訴事件之性質及各國之立法例而不能盡同。其為契約所生債權之效力,則立法例及學說約有四種:有以訴訟地法為準據者、有以債務者之住址地法為準據者、有以履行地法為準據者、有以契約地法為準據者,其第四種主義,在條理上較為允當,為多數國所采用。現在民國關于國際私法之條規未頒行,自應由審判衙門擇用至當之條理,以為适用法律之準據。”本案中契約恰在國内締結,因此法官則選擇主流觀點“契約地主義”,而适用民國法律斷案,有利捍衛了中國之主權。同時,法官在适用的過程中将其轉化為條理賦予其正當性,是以肯定了學說作為第三位法源——條理的補充性地位。
另外,法官也會結合學說創設規則。關于此點,将在後面讨論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方法處詳細闡釋,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三)演繹法律原則
法律原則是在法律規則缺位時,法官進行漏洞填補或排除适用某一法律規則的重要标準。但法律原則由于本身的抽象性而無法直接作為裁判依據,法官必須結合實際案情對之具體化為規則後方能适用。在此,我們必須承認法官造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大理院的推事們正是在審判之時運用所學,以法律原則為基礎創設出新的學說并将其作為“法律規則”适用于裁判之中。這裡,筆者以大理院對情勢變更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的靈活适用為例。
1.适用情勢變更原則
情勢變更原則淵源已久,在12、13 世紀注釋法學派的著作《法學階梯》中就已出現了“情勢變更”條款的身影,近代兩大法系的主要國家均在立法與判例中确立了這一原則。情勢變更原則的運用對于維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促進交易公平有着重要作用。
在大理院8 年上字第1451 号判例中,德商瑞記銀行借款給上告人并約定以英鎊計價分三期償還,委托被上告人湖南管理敵僑事務所代為收款。其中第三期債款逾期未償而恰逢英鎊彙率跌落,被告人因此訴請上告人依照約定按第三期支付日期時英鎊彙率折算漢銀進行償還,上告人則以第二期債款逾期時是按照實際付款日之彙率折算為由予以反駁。法官審理後認為:“合同既在英金不通用之地(即長沙)所訂立,而其前一、二兩期之價金亦按磅價折合交付,則解釋兩造立約之真意,實系以折付當地通用之漢銀為目的。而其折付漢銀除有特約外,即應以支付日期日磅價為折算之标準。”此外,上告人之主張不能認為另立特約許可以實際支付日之彙率為折算标準,是以支持被上告人之訴求。法官的這一判斷很有可能是借鑒了《大清民律草案》,其第 329 條規定:“以外國通用貨币指定債權額者,債務人得依支付期及支付地之市價,以中國之通用貨币支付之。但以外國通用貨币之給付為債權标的者,不在此限。”
有趣的是,在早些時間的一起類似案件中,法官就通過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運用對《大清民律草案》中這一規定進行了變通。在大理院 7 年上字第 361 号判例中,蕭鑒塘将典與李夢奎之房屋賣與遲善卿,合同以外國貨币羌帖(俄羅斯盧布)表示标的額,李氏不服主張先買權。法官認為,李氏出價應與蕭遲二人約定之盧布的實際價額相當,方可享有先買權,乃出賣人不至有所損失。本案争訟之時亦逢盧布驟然貶值導緻與原定價格出入較大,此時法官并未固守《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規定,而是認為:“按民事法條理,凡以常用之外國貨币表示其給付額者,其立約之真意,本不過以該币為計算當時價格之标準,故嗣後給付之時,倘其價格漲落懸殊為當事人始料所不及者,自應仍以約定當時該币所值之市價為标準。”大理院為了保護出賣人的利益不因外币貶值而遭受損害,基于情勢變更原則對《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規定進行了創新性改造,以合同成立之時的外币彙率計算價格,在确保合同目的得以實現的同時促進了交易公平的實現。
2.适用契約自由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作為三大私法原則之一,對于維護人格自由、促進交易至關重要。契約自由原則中以内容自由最為重要,例如當時大理院曾認可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土地使用期限而無最長期限之限制,這在現在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例如大理院對永佃權存續期間的認定。在大理院 2 年上字第 140 号判例中,姚震法官認為:“永佃權系本屬物權性質,故其所訂特約,如不能解釋為有一定期間或已聲明為永久者,則法律上既無最長期之期限,即得永遠存在。”關于佃權可否永遠存續,法官以為若依法律與習慣均無所限制,當事人即可自由約定土地租賃期限。《大清民律草案》第 1089 條規定:“永佃權存續期間,為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原因在于“設定永久無期之永佃權,有使土地所有權陷于有名無實之弊,故無期之永佃權,為法律所不許”。第 1090 條進一步規定:“設定行為未定永佃權存續期間者,除關于期間有特别習慣外,概作為三十年。”這裡,法官并未将《大清民律草案》的規定采為條理,而是借着對契約自由原則的肯定,創造了新的學說,即否定對永佃權設定最長存續期間的限制。
關于地上權的存續期間,大理院也持一緻态度。在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900 号判例中,姚震法官同樣認為:“地上權存續期間,現行法上并無最長期限之限制,故當事人間以合意設定永久存續之契約,亦非無效。”審判衙門亦不能濫用職權,擅自為其酌定期間。盡管《大清民律草案》第 1076 條規定:“設定行為未定地上權存續期間者,審案衙門因當事人起訴,于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之範圍内,酌量其工作物,或植物之種類,及一切情形,定存續期間。”法官仍未采納。但在大理院 5 年上字第 1211 号判例中,餘棨昌法官卻采納了《大清民律草案》的規定中的部分精神,認為:“關于地上權之存續期間,在現行法令上尚無明文之規定。若該地亦無關于此項事實之習慣法則,則本院以為地上權之存續期間,以其權利自身之性質言之,其期間不宜過促,故于此酌定相當之期間。在以建造房屋為目的設定地上權者,則推當事人設定之意思,自應以設定之字據成立時,預計建造之房屋得以利用之時期以為标準。例如當事人于設定地上權時,預定為建築磚瓦房屋,則預計得以利用之時期長,即存續期間亦應長;反是,若預定建築草房或土房,則預計得以利用之時期短,則存續期間亦應短。執此以定地上權存續之時期适合于當事人設定時之意思。”[58]按此要旨,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應當先有當事人自由約定,但應根據實際利用需求加以一定限制,否則地上權人于約定期間内自由轉讓權利會有損害所有權人利益之虞。不過,大理院仍然沒有對地上權存續期間加以最長期限的限制,而認為應當結合當事人的約定以及土地的使用目的對地上權存續期限進行雙重判定。
對永佃權與地上權設置最長租賃期限,一方面是為了保護所有權不被虛置,另一方面,在當今社會主義國家,土地作為公有資源自不能長期占于私人之下。然而事實上,永佃權的設立“幾乎從所有權中抽走了所有内容”。地上權也是如此,“隻要地上權仍然有效,也就實際并存着兩個所有權”。因此,對其設定最長期限的限制并無實體上的意義。加之民初之際,土地為私人所有,所有權人對其自由處分無可非議。大理院早在裁判中指出:“當事人關于自己之權利得以自由處分,乃民事法之大原則。”大理院法官通過對契約自由原則中“内容自由”的肯定,排除了設立最長期限的規定對當事人處分權利的幹涉,并通過條理的形式将這一學說見解上升為具有約束力的一般規則。
總言之,大理院為了彌補法律規則的空白,減少直接适用外國立法例帶來的不合理性,直接訴諸最具普遍适用力的法律原則創造出新的學說來解決本土問題,是在當時應對司法中無法可依之困境的一則妙計。
(四)推行法律精神
法律學說作為法學體系的組成部分之一,“具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規定性,它的産生、發展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相一緻,并受到它的影響和制約”,其發展變化的過程本身也反映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法律精神的變動。因此,法律學說發展的背後所體現的法律價值取向亦是大理院适用學說時所看重的一方面。大理院對于“私權社會化”法律價值的推及恰是一很好的例證。“近代中國民法體系構建之時,恰逢‘私法社會化’思潮在西方盛行并播遷至中國。”19 世紀末期,《拿破侖法典》所确立的“私權神聖原則”随着西方資産階級的壯大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加之社會主義法學的興起,各國紛紛修改法律對所有權絕對原則實行一定限制。大理院在司法之中,既要擺脫傳統重公權輕私權的傳統,又要适用潮流兼顧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在中西法律文化碰撞激烈的民初社會,大理院借由學說實現對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例如在大理院 12 年上字第 1894 号判例中,被上訴人(所有權人)租與他人的機件被租賃人擅自典當給不知情的典當行(即上告人)。關于被上告人如何取回原物,原審法院錯誤依據《大清現行律•名例下 • 給沒贓物》條例,認為該機件類屬于“強竊盜賊”之贓物,應由侵權人賠償典價并由所有權人無償取回。對此,大理院認為機件屬于“輾轉租得之物”,不能與“強竊盜賊”之贓物一概而論,而應适用現代法中善意取得規則由被上訴人封價取回。為此,大理院引用學說對所有權保護模式進行了對比:“誠以社會進化,法律觀念自亦變遷,故各國立法例及學說多變,其昔日絕對保護所有權主義,而着眼于保護交易之安全,雖關于此法則之如何應用,因觀察點各殊,尚非一緻。有偏重保護交易之安全者,即無論所有人之喪失占有是否由于己意,隻需取得人于占有之始,系善意無過失,即令其取得所有權,此假稱為絕對保護交易安全主義;亦有于保護交易安全之中,仍寓保護所有權之意者,此主義複因所有人喪失其所有物之占有是否由于己意有所不同,即(一)由于己意者(如寄托之類),若取得人于占有之始系善意無過失時,即令其取得所有權(參照德國民法 932 至 934 條、日本民法 192 條、195 條、瑞士民法 930 條、民律草案 1278 條)。(二)不由于己意者(如盜髒遺失物之類),其主義更細别為二:(甲)取得人在原則上不能取得所有權,尚許所有人于相當時間期間内請求回複原物,而例外則如取得人系由拍賣場,或公共市場販賣同一種類物品之商人善意買得者,仍不許其回複(參照德國民法 935 條、民律草案 1279 條);(乙)無論取得占有之情形如何,應許所有人于相當期間内請求回複原物,惟取得系于拍賣場或公共市場販賣同一種類物品之商人善意買得者,則需所有人賠償封價,始能請求回複(參照日本民法 393 及 195 條、瑞士民法 934 條),此假稱為相對保護交易安全主義。凡此種種,在學理上有無絕對之是非姑且不論,要其為所有權追及效力之一大例外,不能不審度國情,因時取舍,則無可疑。” “現在一般人之信念縱或保護所有權之觀念甚強烈,然社會進步交易頻繁,苟非懲于向來絕對保護所有人之弊,于一定條件之下保護善易之取得人,則交易之安全且将不保,而社會之安甯于以擾亂。故租主以其租得之物擅行出典,上訴人(即典主)之典受該物果系善意,而該處典商習慣又并非如被上訴人主張,非有保家不能典受,則被上人出資回贖,固不免為一種意外之損失,然亦隻可咎當日轉租之不善,以視善意之典受人對于典物不能一一辨其來源,若不問其是否善意及習慣上有無取保之義務,概得于典後任憑主張所有者無償取贖,不但同為意外之損失,且其害于交易之安全,影響于社會者勢将更巨,兩害相形,自應權衡輕重以為取舍。”
盡管“物歸原主”是一種傳統美德,但在法制社會下審判官不得不在社會公益(本案中指交易秩序安全)與個人私益之中作出權衡取舍。大理院不厭其煩對所有權保護之理論學說的變遷進行了大量闡述,實際上是為了使“私法社會化”的精神滲透到民初法制的發展之中。“善意取得”作為限制所有權的一項重要制度,“正是基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證成了對所有權神聖原則的限制”。
縱觀西方社會法制之發展,經濟變化對于所有權的保護程度影響甚巨。19 世紀,個人主義之風正盛,“在反對封建王權對私人财産的侵犯,保護個人财産、安全和自由,促進商品經濟發展方面,絕對所有權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随着資産階級革命的蓬勃運動,絕對保護所有權使得财富積聚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問題凸顯,“正是民法和私法調整機制的不足以及‘個人本位’和‘所有權絕對’法律思想的泛濫,導緻了社會弱者生存困難、勞動者生存狀況不斷惡化和勞資對立等嚴重社會後果”。為此,對所有權的限制不僅從經濟發展,也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進行了調整。因此,大理院不能以社會初解放為由盲目推崇所有權絕對原則,更要兼顧對社會利益的考量。大理院的法官們敏銳地認識到了這一曆史趨勢,通過對各國立法例背後所代表之學說進行比較,令司法結果更符合社會發展潮流,避免了司法開倒車之窘境。
四.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方法
大理院在适用法律學說時依據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主要分為兩類情況。一是運用法律學說解釋法律,這裡并不涉及學說是否有拘束力的問題,因此法官通過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将學說融入到審判之中;二是引用或創造學說作為法律依據,以學說作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規則時,為了确保适用學說的正當性,法官可以以其權威地位直接将其轉化為條理,抑或是在已有學說的基礎上進行變通并加以充分的論證。
(一)援引學說進行論證說理
法官在援引學說進行論證說理時,學說的主要作用在于縮短具體法律條文與實際案情之間的距離,提高裁判依據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增強裁判的說服力。此時,學說并非直接具備法律效力,而是輔助具備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據得以合理适用。
1.直接引用
一些對于本土來說尚不熟悉但在域外已經形成共識的法律概念與理論,大理院可以直接引用通說而不必過多闡釋。
例如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2118 号判例,本案中被上告人因燒山種樹而失火延燒至上告人的山林造成損害,法官認為确定賠償責任的關鍵問題在于被上告人對于引起火災是否存在重大過失的情形,第一步即是對何謂重大過失進行理論闡釋:“重大過失即欠缺輕微注意之謂,故僅須用輕微注意即可預見有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而竟怠于注意,不為相當準備者,即不可不謂為有重大過失。” “重大過失這個概念,在民法上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但傳統理論認為,重大過失概念的關鍵點即在于違反基本注意義務。德國民法理論中雖有重大過失的概念卻無明确的定義,判例上認為重大過失的認定必須以行為人在主觀上有嚴重不當為前提。大理院依據通說認為,重大過失的認定應依據主客觀兩方面: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對損害存在認識可能性,即欠缺“輕微注意”;客觀上則以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有效防範措施為基準,即是否“為相當之準備”。由此,應當進一步調查被上告人燒山時是否開辟火路(火路是否過窄)以及有無雇傭防火人員等情節加以判斷。
在大理院 5 年上字第 1293 号判例中,為了判斷被上告人對上告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償權,法官先對代位求償權産生的原因進行了學理闡釋:“代位清償之原因本有二種,契約上之代位,除應得債權人同意外,固非通知于債務人得其承諾,不能發生完全對抗債務人之效力;若法律上之代位,則以清償人之清償實有法律上正當之利益為成立之要件,苟已具備此要件,即不問曾經債務人承諾與否,均可取得代位之權。”[75]本案中,法官認為被上告人作為上告人的保證人替其清償債務後,其代位求償權的産生屬于法定代位。代位清償制度起源于羅馬法上的“訴權讓與的權益”,其中即包括了保證人代為清償的情形。大理院将代位産生的原因分為意定代位與法定代位,應是借鑒了法國民法。《法國民法典》第 1249 條規定:“第三人向債權人進行清償後,對債權人權利的代位,或者為約定,或者為法定。”并在第 1250 條與第 1251 條中分别詳細規定了約定清償與法定清償的具體情形。第 2029 條規定:“已清償債務的保證人,代位債權人取得其對于債務人的一切權利。”此規定是受“債權法定轉移說”的影響。因此,大理院在這裡引用法國民法理論中對代位權産生原因的分類進行了論證說理。
2.間接引用
法官在進行論證說理時,為防止對個案的審理帶有過多的學術争論,招緻當事人以及社會對裁判權威與公信力的質疑,在引用存有多個觀點的學說時會盡量避免展現學說的來源。
例如侵權行為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在 19 世紀初便有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說等學說,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究竟該适用哪個則全賴法官的主觀見解。在大理院 2 年上字第 119 号判例中,被上告人因上告人糾衆毀損其耕作物而請求賠償,然原審并未查明案情是否屬實,大理院法官隻好先就侵權賠償責任确定标準進行解釋:“按損害賠償債權之發生,須具備各種要件:(一)有損害發生的原因事實,即損害之本于不法行為者,須有侵權行為;(二)損害發生;(三)相當之因果關系。此種條件具備,始發生賠償之義務,此定例也。”這裡,法官認為賠償責任的發生是指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并且采納了 19 世紀末流行起來的“相當因果關系說”。
關于這一理論,其他法官卻持有不同意見。在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4 号判例中,對于侵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法官認為:“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其構成要件有三:一為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二為被害人之損害;三為故意或過失與損害之因果聯絡。三者有一不備,斯賠償之責任無理由成立。”顯然,這裡法官認為侵權賠償責任之确定要求的是行為人過錯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不法行為與過錯并非完全等價之概念,例如德國法中就規定了違法性、過錯、損害事實與因果關系四要件,并且關于因果關系的認定标準似乎也與前案不同。雖然本案由于缺失全文無法進一步考證,但通過與前一案例的對比已足以顯示不同學說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影響。
這兩則案例中,法官顯然借鑒了不同的因果關系學說進行論證說理但并未直接體現,這一做法一方面是為了确保大理院的權威不緻令當事人感到不公正,另一方面也與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氛圍有一定關系。民國時期法學學術研究氛圍自由,大理院的法官們深受學術研究的影響,甚至其本人亦是學者。在法學研究的過程中,“民國學者更明顯地淡化了‘中外二元對立’和‘一般法律問題’的相互勾連”。“将外國法律文化包括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話語霸權,悄悄地放逐,因為,這些民國學者,不甚在意外國或中國傳統的法學、法律所說,而是直指實際的法學、法律問題,并在細密辯駁的基礎上,展開法理推論。”大理院的法官們在司法中刻意回避學說的來源,或許緣于此,雖然存在着法官價值判斷失衡的風險,但就民初法制的特殊背景來看,尚無可厚非。
(二)運用學說作為裁判依據
雖然學說在曆史上曾被直接付與法律效力,“然至于近世國家雖認學者之學說,而即據以為法律者,實未見其例”。但是民國初期的成文法疏漏不全,大理院在司法裁判之際有時直接引用學說亦是迫不得已之事。唯在适用學說的過程中,要加以充分論證或是借助條理的法源地位,才能使學說獲得法律拘束力。
1.變通學說創造規則
盡管法律學說是法官無法可依時的重要參考,但對其采用之時亦必須慎之又慎。畢竟,“法學通說大多受到法域實證法的影響,其在強調普遍共識的基礎上,一般也具有法域性的特點”,若不考慮本土現實而徑直适用則無法令當事人信服。例如當時由于登記制度尚未實施,在幾起有關不動産物權變動效力糾紛案件中,法官就對域外通行的登記生效主義與登記對抗主義進行了适當的變通取舍。
在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142 号判例中,申氏将被上告人祖先贈予的田産轉賣于上告人,被上告人以原贈予契約中附有“禁止當賣”條款為由請求認定買賣契約無效。本案的關鍵問題在于上告人能否以善意取得而對抗被上告人。為此,法官認為:“按民法法理,物權得對抗第三者,其依法律規定而登記之債權,亦有對抗第三者之效力。我國民法尚未頒布,物權應有幾種,以及何種債權得有對抗第三者之效力,本屬(值得)研究(之)問題。而依一般慣例,凡不動産轉移,必交付手上契約證明該不動産并無他轇轕之要件,藉以補無登記制度之窮,法至善也。”本案中,法官認為登記制度缺失時應當通過其他契據作為登記行為之替代。據此,上告人買受不動産時應當查明并轉移相關契據(本案中是指原贈與契約)方可對抗被上告人。然而,申氏違背贈予契約中的限制條款未經被上告人同意而出賣田産,法官認定為無權處分。同時,上告人亦未履行注意義務移轉契據,存在重大過失(惡意)。因此,法官認為:“以附有限制之贈予田産,誠使上告人索交上手契,即有可以注意之機會,乃并不問其權源,若貿然承買,被上告人根據贈與契約出而抗議,其主張自屬正當。”登記的作用在于公示,大理院亦明白此理。但在法律缺位、制度未備的情況下,法官則主張以産權契據和轉手契等文書代替登記的公示作用。
實際上,對于不動産物權變動效力,《大清民律草案》第 979 條規定:“依法律行為而有不動産物權之得、喪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其立法理由中闡述了地券交付主義、登記公示主義以及登記要件主義三種不動産物權變動方式。在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127 号判例所記載的一則“一田二賣”糾紛中,上告人主張買賣在先而取得所有權,被上告人則主張借鑒登記對抗主義以稅契代替登記行為:“況自法理言之,凡物權設定轉移欲對抗第三人,在不動産以登記為要件,非所論于購産之先後。中國稅契辦法實與登記相同,效力亦正相等,本案上告人既始終未嘗為合法稅契,縱謂購産在先,亦無對抗第三人之效力。”法官卻不以為然:“至于稅契并非對抗第三人之要件,不過公證書之一種,以之證明買賣典當關系成立之真實,自不能與外國法之登記可以相提并論。蓋現行法上當事人間如有合法之買賣,則物權即已轉移,可以對抗第三人,更無須有他項要件之存在。”可見,法官在此似乎是采取類似地券交付主義的标準進而認定先買人享有所有權。另一方面,以是否繳稅代替登記可能會對買受人課以較重的審查義務,既不利于買受人亦有礙于物的流轉利用。
此種問題同樣出現在擔保物權競合糾紛之中。在大理院 5 年上字 887 号判例中,上告人以登記對抗主義為由主張對典産享有優先受償權:“凡在同一目的物上之權利,種類相同者,自由優劣之别,若此數種權利效力相沖突時,其發生在前者,當然有優先之效力,此通例也。”但是法官卻認為:“二人在同一目的物上先後取得擔保物權者,若後之擔保物權人系善意且無過失,則因登記之制迄未施行,權衡利弊之輕重,而保護交易之安全,固應使其就目的物之賣價,得以按照比例,受同等之清償。”這裡,法官顯然明白登記對抗主義的價值所在,但是礙于登記制度尚未建立,又想要兼顧當事人的利益,斟酌之下認為擔保物權競合時若在後擔保物權人并無惡意,則可由數個擔保物權人按照債權比例受償。
盡管不動産物權變動登記對抗主義在近代大陸法系國家被普遍承認已形成通說,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仍不能在登記制度施行前直接适用,否則無異于事後立法,有害于當事人對法律的信賴利益。因此,為了緩和法律上應然與制度上實然之差距,即便是域外通說也應結合民初的實際國情适當變通以更好地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
2.将學說轉化為條理
更多情況下,大理院會憑借其權威地位,将所運用或創造的學說以條理的名義直接适用到審判結果之中,既減少了論證的負擔也能夠迅速解決糾紛。
首先,可以一則典産糾紛為例。典當作為傳統民事制度之一,卻被《大清民律草案》所抛擲不顧。大理院卻并未生硬地将其他擔保物權的規定用之于典當關系之中,而是尊重典權的特殊性,在現行律無有關規定時發揮創造力對相關問題進行裁判。在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1760 号判例中,典産因典主(典權人,本案被上告人)失火而被焚毀,關于如何分配損失,即原主(原所有權人,本案上告人)依何标準取贖的問題,現行律并無明文規定。巧合的是,在一起類似案件中,法官曾将前清乾隆十二年間一則判例要旨引為條理,該要旨稱:“典産延燒,其年限已滿者,聽業主(所有權人)依照原價減半取贖。”不過,該規則主要适用于因鄰累不測而緻典産延燒的情形。而本案的不同之處在于,典産系由典主失火焚毀而非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事由。因此,當事人雖曾在合同中約定:“設遇鄰累不測,則原主造完房屋,與典主無涉”,但法官認為:“由典主失火焚燒者,即非約載鄰累不測之情形可同論。”所以不能依據原約仍由原主承擔全部損失。為了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法官在該要旨的基礎上結合過錯原則以及公平責任原則創造了一全新規則并引為條理:“茲姑以條理言,本院以為凡典産年限已滿不贖、典産延燒,而典主未為起造新物者,應由原主依照原典價減半取贖。即對于焚燒之屋,典主須負擔原典價半額之損失;如系由典主自行失火,并非故意者,則其責任,亦須分别過失之等次(重大過失、普通過失、輕微過失)稍與加重,應聽原主不付典價消滅典權(重大過失)或以原典價四分之一(普通過失),或三分之一(輕微過失)贖取。即典主負擔之損失,在重大過失時為全典價,普通過失時為四分之三,輕微過失時為三分之二,此其分配較為公平,而考之往昔,亦有先例。”這裡,法官對舊律内容進行了創新性改造,将典産延燒的損害賠償責任擴大到當事人之間存有過錯的情形。
将學說轉化為條理,還可以參見大理院對“買賣不破租賃”這一原則的适用。“買賣不破租賃”成熟于近代民法,旨在強化對承租人的保護并促進租賃物的有效利用而為近代各國所承認。但是關于租賃權的性質,即得以對抗買受人的原因,理論上主要有租賃權債權說、租賃權物權化說、租賃權物權說等多種觀點。在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455 号判例中,被上告人因取得系争房産的所有權而請求判令上告人(即承租人)退屋撤租,而法官認為:“按民法條理,不動産所有權人得對其所有權附以限制條件,或就其使用、收益權而為一部分之處分,此項處置若依法可認為物權之設定者,則所設物權于不動産轉移時,不惟對于承繼人或受贈與人仍屬繼續有效,即對于買主亦有對抗效力。”據此可以推論,大理院法官認為租賃權本質上為物權的一種,因此可以依據物權優先原則對抗其後的物權行為。顯然,大理院此時運用的條理是“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中的租賃權物權說的具體展現。無獨有偶,這一學說亦體現在大理院對佃權與所有權轉移相沖突時的處理之中。佃權,支付佃租而于他人土地上為耕作或畜牧,利用他人土地之物權也。永佃關系本質上不過是長期租賃之一種,因立法行為而獲得物權效力。在大理院 4 年上字第 1117 号判例中,法官即認為:“按現行法例,所有權與永佃權為個别之物權,所有權轉移,佃權當然不能消滅。故如以所有權讓于他人,并與讓受人為消滅佃權之契約者,其契約不能對于佃權人生效,自不待言;即因該契約履行之不能,緻讓受人受有損害者,亦隻許讓受人向讓與人請求賠償,斷無令讓與人賠償佃權人而将佃權消滅之理。”本案中,法官不僅認為佃權屬于物權,更進一步表明這種物權關系并不破壞租賃人與原所有人之間債權債務相對性的關系。換言之,租賃權物權說雖本質上将租賃權認定為物權,但并不會因此導緻原有租賃關系因所有權轉移這一物權行為而受到破壞。
大理院将學說轉化為條理,從法源的角度為學說找到了栖身之所,确保了以學說作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五.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意義與影響
民國伊始,法律不備,學說再度成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大理院以條理之名一邊引入學說,一邊創造學說,方得以使每一個無法可依的案件能夠圓滿解決。大理院所運用的學說的内容成為日後立法、司法的重要參考,“許多具有标志性的意義的民事判例原則,不僅為 1930 年代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院創制民法典時所采用,在司法實務上也直接成為各級法院審判的法源依據”。
(一)影響後續之立法
從立法的角度看,“不僅判例法的構建需要法律學說,成文法的具體化和體系化更離不開學說”。在無成文民法典可供參考之際,大理院于司法中運用法律學說架起了實踐與立法的橋梁。
一方面,大理院裁判中引用的學說為日後的立法提供學術資源。例如大理院 2 年上字第 238 号判例中,法官認為:“凡法人之設立有自由設立主義、特許主義、準則主義之區别。其采用準則主義者,法律中特别規定法人成立一定之準則,必合乎法定準則者,法律始認其成立,然此亦衹對于法律施行後新設立之法人為然,若于法律施行前曾經認為成立者,則依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仍不得不設例外之規定,此關于法人有明文規定之國家之常例;至于無明文規定之國家,應否于法律上容認法人之成立,本屬待決問題。惟法人之存在,本為社會上自然發生之事實,社會因種種之必要而發生特種之現象,國家惟有制定法則謀所以規之,斷無根本上加以否認之理,故若法律并無認許及限制明文,而在事實上别于個人有應獨立享權利負義務之能力之人類集合體,或财産固定體,當然不能不以為法人而認許其存在。”關于法人的成立,《大清民律草案》中法人一章通則部分第 61條規定:“社團及财團,得依本律及其他律成為法人。”即采取準則主義。社團法人一節第 67 條規定:“社團法人有經濟上目的者,其設立及其他事件,依特别法之規定。”第 69 條規定: “設立社團法人,無經濟上之目的者,須經主管衙門允許。”分别采取準則主義與特許主義。财團法人一節第 143 條規定:“設立财團法人須經主管衙門允許。”即采取特許主義。然而《大清民律草案》并非現行法,對法人資格的認定仍要結合訴訟主體的形式與性質從理論上加以判斷。在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1235 号判例中,法官就肯定應當從團體實質屬性的角度賦予其法人資格:“按民國法律未備,關于公法人、私法人之設立尚缺乏明文規定,惟法人非法律之創設物,凡為一定之目的,各人以類集合而成有組織體,則法人之本體即具,實際上即不能不認為法人。此民法施行前之變通辦法,而亦至當之條理也。”然正如法官所言,“國家惟有制定法則謀所以規之,斷無根本上加以否認之理”,立法上關于法人的設立問題必須予以完善。在 1925 年的《民國民律草案》中,關于法人成立的規定全部放在了法人一章的通則部分中。其中第 27 條規定:“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及财團,以得主管官署之許可,取得人格。”即采取特許主義。第 28 條規定:“非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及财團,以定立章程發表成立團體之意思,取得人格,但其目的不得違反法律或有傷風化。”增加采取了自由設立主義。第 29 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人格,依特别法之規定。”即采取準則主義。但令人意外的是,1928 年頒布實施的《中華民國民法》則放棄了自由設立主義,僅保留了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成立采取準則主義,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與财團之成立采特許主義。這一直沿用至當今台灣地區的現行民法之中。
由于當時民法理論的匮乏與民法規範的缺失,許多民事主體無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大理院則通過司法實踐,“把行幫、會館、政黨等團體漸次納人審判範圍,逐次加以類型化,把國家導向現代化的路徑上來”,所積累的裁判要旨更是促進了立法對法人這一外來概念的吸收與融合,緩解了近代法律與固有文化的沖突。
另一方面,大理院裁判中适用的學說并非完全适當,而是促進了立法者對于相關問題的思考并制定更加符合社會需要的規範。例如,對于合夥成員之間如何分配損益的問題,《大清民律草案》第 809 條規定:“合夥人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約定者,不問其出資種類及價格多少,平等均攤。僅就利益或損失分配之成數者,其成數視為損失及利益之成數。”依此規定,合夥成員之間可自行約定如何分配損益,無約定時平等分配。但這會導緻在債務承擔時不利于出資比例低的股東,在利益分配時又不滿足于出資比例高的股東,并不公允。大理院也意識到這一缺陷,因而在 5 年上字第482 号判例中,并未照搬前一規定,而是創設一新規則:“合夥債務應由各合夥人按照分攤損失之标準,分别負擔分攤損失,标準未經明定者,以分受利益之标準為準,分受利益标準亦未明定者,則以出資多寡(即股分)為準。”本案中,法官認為合夥債務分擔與利益分配的标準應尊重合夥成員的約定,無約定時則依據出資比例斷定。相較于《大清民律草案》中規定的當事人未約定時則平均分擔的規定,大理院的處理明顯要更加合理。大理院的這一裁判要旨也被《民國民律草案》所吸納,其第 666 條規定:“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合夥人出資額之比例定之。僅就利益或損失一方所定之分配成數,視為損失及利益共通之分配成數。”其後的《中華民國民法》以及當今台灣地區的現行民法均沿用這一規則。
(二)影響後續之司法
民初大理院民事各庭的判例是實質的民事法律淵源,大部分學者對于大理院的判例制度持肯定态度。從司法的角度看,判例且不論性質如何,事實上在大理院裁判中具有實際的法律約束力。學說則構成了判例原始案件中的實質性内容。“原始的判例者,乃是種判例為創制與應用新法者。”原始判例中,“其組成權力原素之暗藏原理,普通稱之曰‘判理’,故具體之判決僅可約束訴訟兩造,而抽象之判理,乃有普遍法律效力焉”。顯然,法律學說是大理院判例中“判理”的重要來源之一。胡長清曾言:“民事法規既缺焉未備,于是前大理院乃探取法理着為例,各級法院以取法之矩各級法院遇有同樣事件發生,如無特别反對理由,多下同樣之決,于是于無形中形成大理院之而有實質的拘束力之權威。”大理院彙編判例要旨時亦肯定了學說對司法實踐的重要意義:“民國以後,大理院一以守法為準;法有不備或于時不适,則借解釋以救濟之。其無可據者,則審度國情,參以學理,著為先例。”無疑,學說以其内容産生判例實質上的拘束力。
例如大理院 3 年上字第 253 号判例雲:“本院按民商事法理,普通民事留置權之行使必須具備二要件:即一其物須為債務人之所有物,二須關于其物所生之債權是也。”本案中,法官首次結合日本學說對德國理論的借鑒認可了留置權的物權屬性和債權效力。其後,在大理院 5 年上字第 301 号判例中,大理院則沿用這一要旨:“凡占有他人之物而關于其物生有債權者,至其債權受清償為止得留置其物,并得以該物之孳息充其債權之清償,且此項留置權系屬物權性質,對于受讓該物之人亦得主張之,此民事法上之條理,疊經本院判例采行者也。”在大理院 14 年抗字第 89 号判例中,大理院亦表示:“留置權利除奧、瑞、日本外,歐美各國立法多不認為物權,誠如再抗告論旨所稱;惟本院曆來判例為保持公平、促債務人清償起見,已認留置權利為債權之特别效力(參照三年上字一号、三年上字二五三号、五年上字三零一号判例)。”是以直接表明前有判例對後續司法的重要影響。同時,大理院以“優先權之外更有優先權”之理肯定了留置權對于其他擔保物權而言具有優先性。大理院以其權威地位,将學說通過判例的形式固定下來,确保了新式法理能夠于立法采納之前被司法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新舊社會變遷中的法律沖突。
從長遠來看,大理院以學說為論證資源釋法說理,發布解釋例的做法對當今我國台灣地區的司法有着不可言狀的微妙影響。“最典型的是台灣地區的‘大法官解釋’,幾乎每篇都會伴随着中外法律學說的援引。”其實在古代中國,為了尋求裁判依據,除儒家學說作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外,私人對法律的注釋和闡發也是司法過程中參酌的标準之一。滿清時期,“‘私家’注律成果一般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某些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律學著作,或由長官作序,或薦至官方書局刊印,尤其是沈之奇所著《大清律輯注》被冠以欽定”,從而成為不可或缺的裁判依據。“清末民初恰處于這樣一個特殊的階段,為了克服法制不備的困境,大理院推事諸君選擇并運用‘判例’與‘解釋’的方式,擔負起‘準立法’的雙重任務。”除了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域外通說與适時創造學說,大理院亦将學說融入到“判決例”與“解釋例”當中,指導各級法院的司法審判。郭衛在彙編大理院解釋例時曾說道:“此十餘年中,正值我國改良法律之時期,各級法院對于民、刑事件之疑義滋多,而大理院之解釋亦不厭長篇累牍,論述學理,引證事實,備極精詳。”這一慣例使大理院作為司法機關始終掌握着法律解釋權。1928 年頒布的《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司法院院長享有解釋法令與變更判例之權。1947 年 7 月 21 日通過的《司法院組織法》則設立“大法官會議”,專門負責解釋“憲法和法律、法令”:“司法院設立大法官會議,以大法官九人組織之,行使解釋憲法并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大法官移植德國公法學以及美國憲法學理論通過一系列‘大法官解釋’完成了比例原則的建設”,在釋字第 771 号解釋中,羅昌發 (1 次)、許志雄(4 次) 、詹森林(7 次)、蔡明誠(30 次)都通過寫入正文或腳注的方式援引學說;在釋字第 776 号解釋中,分别有湯德宗(1 次)、許志雄(1 次)、蔡明誠(4 次)通過腳注形式援引學說(括号内為援引學說的次數)。大理院援引學說發布解釋例的做法或許正是這一制度的濫觞。
六.結語
民國初期,傳統法律凋敝不合時宜,移植于德日的新民法又尚未成型,在民法法源缺失不備的情況下,大理院适機引入學說彌補法律的不足。“學理思想,為法律之要素,其功用有二:一則有補救法律之功用;一則有創造法律之功用。或曰:一則為舊法律之改造;一則為新法律之創造。”大理院在司法實踐中對學說的适用恰基于此,既征引來自異域的法律學說傳播了近代歐陸法概念與理論,又立足于本土國情創設新學說作為“法律規則”推動社會平穩過渡。大理院援引法律學說的司法實踐,對民國時期的立法與司法均有着長遠的影響,其嚴謹細密的論證說理風格時至今日仍影響着海峽兩岸的民事司法。
近代以來,西方法律思想紛至沓來,融情于法的中華法系潰于一夕。在無成文民法的困境下,大理院借由條理這一多元包容的民事法源,為司法審判提供了彈性空間。法律學說作為條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其理性進步的一面連接起法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同時緩和了西方法律理念對傳統社會秩序的沖擊。大理院适用法律學說的過程,不僅僅是對理論的實踐,更是對中西法律文化與價值的傳承與融合。一直以來,法律學說都是立法的重要參考,而法律的進步亦為學說進行理論創新提供動力,但法律學說作為重要的法律資源,其地位在我國仍暧昧不清。大理院作為民法近代化的先驅者,其運用法律學說于司法審判的思想與智慧,在百年後的今天仍值得“溫故而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