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2年第3期(總第5期)“學術專論”欄目
【作者】趙香如,2003网站太阳集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湖南省刑法學會常務理事。
【摘要】運用 SPSS 模型檢測發現,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在量刑情節适用上存在涉黑主體差異、地區差異等問題。建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常态化量刑情節适用機制必須從理念層面思考,摒棄從寬情節不适用于重罪犯罪分子以及認罪認罰制度不适用于重罪的偏見,并在實證基礎上确立人身危險性的實質認定标準。
【關鍵詞】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量刑差異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在智慧司法及量刑規範化改革領域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但刑罰理論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仍有必要強調。刑罰理論制約犯罪理論,“刑罰論是建構犯罪總論的起點,犯罪概念的内容取決于刑罰的正當化根據”。然而當前我國有關掃黑除惡的學術成果基本局限于犯罪性質的認定,盡管也存在極少數刑罰适用的探索,但基本上局限于犯罪認定研究的慣用思維——定性研究方法。此類研究成果豐富了法教義學内容,但難以滿足刑法追求實用效果的強烈欲望,“為了适應刑事司法的需要,刑法必須從司法實踐中汲取更多營養”。刑法如果營養不良、效率低下,則很可能是“在刑法的創制、審判以及執行判決過程中不能使用預測領域的科學成就之結果”,因為“像其他社會科學的分支一樣,法律上結論的有效性隻能用概率邏輯而非确定性邏輯來驗證”。因此,在我國掃黑除惡專項鬥争取得卓越成績之際、在常态化掃黑除惡機制納入我國“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标的關鍵時刻,檢測我國掃黑除惡專項鬥争中的量刑偏差,并從理念上予以矯正,對于建立掃黑除惡常态化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何選取分析樣本,我國學界尚無通用的範式。當前國際學術界普遍采用複現邏輯。根據該邏輯,“案例的選取要具備典型性、反映研究的政策取向、涵蓋不同的地理區域,尤其是不同經濟地帶”。據此,本文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江蘇、遼甯、湖南、河北、雲南、甘肅六省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裁判文書進行分析。由于案例上網有滞後性,2021 年刑事案件僅 23 例,因而檢測時間設定為 2018—2020 年掃黑除惡專項鬥争期間。樣本案件共 883 份,清洗後有效案例 395 個、犯罪人 2237 名。
一.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分布
量刑通常指人民法院确立報應刑之後依據量刑情節裁量預防刑,并最終确立宣告刑的司法過程或行為。盡管預防刑至今飽受學界質疑,但并合主義仍為大多數國家刑法理論和實務之通說,“沒有脫離預防思想的絕對報應,也沒有脫離報應思想的絕對預防,從更深層次上說,報應與預防的關系是正義與功利的關系”。宣告刑也就應為責任刑和預防刑的複合物,為此量刑情節無疑是決定宣告刑的關鍵因子。然而哪些因素可以充當量刑情節,理論和實務界均無統一标準。通說認為,量刑情節包括行為人的人身特征,如“有無前科 , 是否屬于累犯、再犯,犯罪人的性格(是否具有常習性)、一貫表現良好與否;犯罪後行為人的态度,如自首、立功,以及是否認罪認罰,被告人的家庭及社會能否接納其回歸,被害人一方的原諒等”。此種列舉不免殘留意猶未盡的遺憾,因而可轉向法治主義原則以求更具有概括性的認定标準。根據罪刑法定的要求,不論是“除罪化”“除刑罰化”、刑事執行“除機構化”,或者“入罪化”“從重量刑”“長期監禁”等都需要在實體刑法上加以解決。當然,刑罰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符合法律精神并在司法實踐得以形成的習慣性量刑情節也應為法治主義原則所包容,“在我國《刑法》中 , 法律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最為重要的一項制度 , 就是酌定量刑情節,它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具有天然的密切聯系”。因而本文對刑法認可和司法實踐公認的情節一并予以梳理。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量刑情節主要有累犯、前科之從嚴情節,認罪認罰、自首、坦白、立功、當庭認罪之從寬情節,其分布及規律如下。
(一)從嚴情節
樣本數據中曾經犯罪者433 人,比例高達 19.4%,其中有 1.4% 的犯罪分子既有前科亦為累犯,具體見表 1-1。

累犯與前科并存是一個還是兩個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規範化實務手冊》,如果在累犯從重處罰幅度内足以達到從重處罰的效果,就可不再單獨認定前科;如果僅适用累犯情節還不足以體現從重處罰效果,可以再單獨考慮前科,對此可概括為“處罰效果決定論”。那麼處罰效果根據“犯罪人”還是“犯罪”來判斷?有學者認為“如果脫離具體犯罪而抽象地讨論量刑情節的單複數問題,實際價值極為有限”。這種觀點看似提出了“犯罪決定論”,但其實質強調不能籠統而應具體評價情節的競合問題,此處犯罪也泛指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類型,而非特指與犯罪人相對應的犯罪行為,因而不能表明其采用了與最高院相反的立場。
如果承認一個常識性的命題:法律本質上是價值判斷,量刑乃對犯罪後果評價。那麼就應肯定量刑情節并非單純的事實性存在,而實質為功能性存在。由此即可推斷,有關情節運用的一切評價均應采取價值标準。若情節用以确定預防刑,則應遷就預防刑的需要,在判斷上自然更應注重犯罪人;若用以判斷責任刑,則應迎合責任刑的要求,如此則更應注重犯罪本身。而累犯或前科均為預防刑裁量情節,因而也就應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确定前科與累犯重合下的情節個數。但後文将深入分析,人身危險性的判斷至今缺乏實證研究成果的支持而流于形式标準,而且除了刑罰規定的累犯、自首、坦白等人身危險性因素影響刑罰輕重外,其他諸如犯罪人的成長經曆、生活環境、世界觀等絕大多數體現人身危險性的因素主要用于犯罪改造,因而在整個犯罪追究過程中人身危險性的實質判斷需求市場并不太大,但其對于量刑活動卻至關重要,其與起點刑共同壟斷預防刑的全部市場。由于依據行為人的人身危害性來解決情節個數問題當前不可行,而隻能參照犯罪的嚴重性來評估。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在刑事政策上是國家重點打擊且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的犯罪,細讀裁判文書發現,相當多的前科未升格成累犯并非罪質不合格,也非前後罪刑期不達标,而因時間間隔超過 5 年。因此,前科與累犯并存應視為兩個情節,本文将其同時計入累犯與前科總量中。
(二)從寬情節
各種從寬情節之間存在一定邏輯關系,因而數據統計前應先對從寬情節予以整合。根據 2021年的量刑指導意見的要求,認罪認罰制度與其他從寬情節并存則提高其從寬比例,同時其他從寬情節不再計算。因為“認罪認罰包含認罪、認罰的一系列情節,不是新的獨立的量刑情節,就認罪情節而言,它與自首、坦白、當庭認罪有重合之處;就認罰情節而言,它與退贓退賠、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亦有重合之處,因此在實體從寬處理上,對重合情節不應重複評價”。後文數據檢測将證明認罪認罰的整合功能對于量刑情節适用的規範化具有重要價值。此外,根據自首、坦白與當庭認罪認定标準的競合關系,如果犯罪人被認定為自首,也排除再次被認定為坦白或當庭認罪。
經上述整合,各種從寬情節的發生頻率分别見表 1-2 至表 1-6。首先,坦白者最多,且高出自首近 3 倍,犯罪分子主動歸案的意識不強,但一旦被動歸案卻也願意如實陳述以争取寬大處理。其次,立功者非常稀少(表 1-5),在筆者統計的其他犯罪中,立功情節也屬罕見,其原因複雜,但在此主要說明,立功情節分量太小不具有統計意義。最後,樣本案例中具有認罪認罰情節的犯罪人共計 316 人(表 1-6),占比 14.1%,而同期該制度的适用率已達 65% 左右。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軍檢察長最近報告,2021 年的制度适用率超過 85%,量刑建議采納率超過 97%;一審服判率96.5%。可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認罪認罰制度的适用比率與全國整體适用率差距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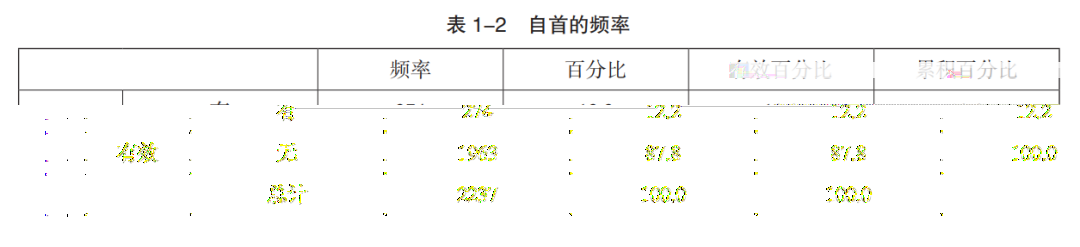


本數據庫依據“法院認為”取樣,即上述情節在事實上已為法院确認,其價值也就應體現在宣告刑中。雖然一定程度上的量刑差異可以接受,但這種差異“必須具有客觀合理性,即事前的可預測性”,因而量刑情節是否适用,以及适用的相對幅度是否合理,有必要以法律為依據進行判斷。為此上述描述具有如此意義:除立功外,其餘情節所占比率均超過 5%,從而均應對不同涉黑主體、不同地區的宣告刑發揮價值,如果未能,則說明量刑情節适用不充分或幅度不合理。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根據檢測結果,在 3 年掃黑除惡專項鬥争中,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人數逐年激增,宣告刑逐年攀高,非參數檢驗結果也較理想,此類數據共同證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刑罰正趨于穩定,走向常規化。而且認罪認罰 2018 年才進入刑事訴訟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2018 年諸多量刑情節均低于 5%,因而就年度而言,量刑情節适用質量檢測無甚必要。為此下文以不同涉黑主體及不同地區量刑情節适用差異為研究對象。
二.量刑情節對不同涉黑主體的适用差異檢測
在統計學分析中,樣本數超過變量 20 倍即可保證統計檢測的有效性和準确性,本模型 8 個變量共有 2337 個樣本,樣本數已為變量的 292 倍,因而數據檢測結果可信度較大。下文以量刑情節為自變量,宣告的自由刑為因變量,區分不同涉黑主體,檢測量刑情節的适用問題。
(一)檢測模型選擇
回歸分析模型的選擇應以自變量與因變量的性質、特征和研究目的為依據。法學界對量刑情節适用質量的實證研究傾向于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依據統計學原理,線性回歸模型要求變量滿足獨立性、線性、正态、方差齊之要求,特别是前兩者為剛需,後兩者可接納近似樣态。根據檢測結果,刑罰因變量具有獨立性、共線性特征(滿足了前兩者),但不具有正态性和方差齊的特征(未能滿足後兩者),因而可以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不過,此因變量為連續變量,自變量均為二項分類變量,能納入比較考察的模型将更佳。考夫曼認為“通過類比,有待認識的事物不是在其自身中被認清,而是在一種它與别的更為熟悉的關聯中被認清”。線性回歸模型隻能單純檢測各量刑情節與自由刑的回歸關系,而不能反映此種回歸關系在不同程度宣告刑中體現的差異。總言之,為了探索不同程度宣告刑與各量刑情節的回歸關系有必要考慮有序回歸與多項邏輯回歸模型。
采用有序或多項回歸建模應将宣告刑轉化取值,設定為有序或分類變量,在此存在以傳統的重罪輕罪二分法和參照法定刑幅度兩種路徑,但考慮到理論和實務界對輕重罪的劃分标準不統一,加之“所有超法律的公理——部分因法律的理性主義,部分因近代主智主義一般性的懷疑精神——普遍地日漸瓦解和相對化”。本文參照法定刑劃分标準,将宣告刑分為三組,分别為 3 年以下輕刑(含 3 年)、3 年以上不滿 7 年中度刑、7 年以上重刑(含 7 年)。我國不存在加重處罰,因而該罪中宣告刑 7 年以上者必定為組織、領導者;而經過檢測組織、領導者适用量刑情節後下滑到 3 年以上 7 年以下,以及積極參者适用量刑情節适用導緻刑罰下滑為 3 年以下者均極少,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因而此兩檔宣告刑分别可對應一般參加者、積極參加者之宣告刑。将數據輸入兩種模型,不僅能經受平行線檢測,最終檢測結果相同。由于有序回歸模型的 OR 值(Exp)需要根據公式手動計算,而多項邏輯回歸模型自帶 OR 值,因而本文最終選擇多項邏輯回歸模型,檢測結果見表 2-1。


上述回歸模型表明,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宣告刑中,量刑情節整體發揮了明顯價值,但是作用于不同涉黑地位犯罪分子,價值卻有差異。
(二)量刑情節适用的充分性
上述參數估算表中無 7 年以上刑罰的回歸數據,表明各種量刑情節對于組織、領導者而言均無意義,為了進一步檢測此結論的科學性,再次對其采用線性回歸單獨建模,模型顯示的P值為 0.293(大于 0.05),從而表明各項量刑情節确實對宣告刑在 7 年以上者無影響。為了最小化檢測誤差,筆者又對組織、領導者的宣告刑與量刑情節進行線性回歸檢測,P 值為 0.118(大于0.05),再次表明量刑情節與組織、領導者的宣告刑不存在回歸關系,至此隻能接受此“不盡如人意”的結論。此情形純屬客觀現象還是司法機關的量刑偏差?如果該地位犯罪分子的量刑情節本身量微,則司法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應将其作為客觀現象來接受,或從犯罪學的視角探讨促使組織、領導者認罪悔罪之道術。但是統計發現,除自首、立功、當庭認罪比率在 3% 以下,其他情節存在頻率高,足夠發揮量刑價值,進而說明,在組織、領導者的量刑中,量刑情節适用不充分。
在 3 年以上 7 年以下宣告刑中,隻有坦白、認罪認罰與宣告刑存在回歸關系,而該地位犯罪分子各種量刑情節發生頻率均較大,足夠發揮量刑價值,從而說明在積極參加者的刑罰中,從嚴情節和酌定情節運用不規範。值得欣慰的是,模型數據表明,在 3 年以下宣告刑中,隻有前科運用不充分,其他量刑情節對于參加者的宣告刑作用均較充分。
(三)量刑情節适用幅度的合理性
量刑情節裁量幅度是否合理?首先應确定判斷标準。在此存在絕對和相對标準,前者指情節本身的幅度值是否符合量刑指導意見要求,後者指各情節之間的幅度序列是否符合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絕對标準适用于就個案進行理性評價,即為幅度,存在适用差異也就無可厚非。但相對标準是從整體上判斷具體情節相對于其他量刑情節而言,其運用幅度是否合理,因而此種不合理是法治主義原則難以容忍的,根據本文研究目的,在此采取相對标準。
根據量刑指導意見,自首的基本從寬幅度為 0~40%,坦白為 0~20%,當庭認罪為 0~10%,認罪認罰為 0~40%,累犯為 10%~40%,前科為 0~10%。考慮到認罪認罰吸收自首、坦白等從寬情節而導緻從寬幅度增大概率較高,各量刑情節影響力大小(不分正負)的應然序列為:認罪認罰 >自首 > 累犯 > 坦白 > 當庭認罪 = 前科。在上述模型中,EXP(β)回歸系數,即 OR 值的大小反映了該情節的作用力大小,根據模型,量刑情節的實然價值序列為:在 3 年以下宣告刑中,認罪認罰 > 當庭認罪 > 自首 > 坦白 > 累犯;在 3 年以上 7 年以下宣告刑中,則認罪認罰 > 坦白。實然與應然對比,表明累犯的實際從嚴幅度不夠,當庭認罪的實際從寬幅度過大,其餘情節的裁量幅度較合理。
綜上所述,以不同涉黑主體的宣告刑為檢測對象,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存在情節适用不充分、量刑幅度相對不合理問題,在涉黑地位高的犯罪分子中,問題尤其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人員對于罪刑嚴重的犯罪分子存在怠于權衡從寬量刑情節的傾向,具有量刑權隐形濫用之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此種量刑權隐性濫用情形非常嚴重,“不同種族、性别、國籍、文化程度的被告在同種情況下所受到的刑罰存在很大的不同,對黑人與其他種族的人的刑罰嚴于對白人的刑罰,對男性的刑罰嚴于對女性的刑罰,對非美國公民的刑罰嚴于對美國公民的刑罰,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被告的刑罰嚴于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告的刑罰”。我國有學者在盜竊罪的實證分析中,也得出結論,“被告人的學曆等被告人的社會結構差異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其作為一種隐性的力量,對法官的定罪量刑默默産生影響,對法律的确定性、公正性和社會正義觀也是一種極大的挑戰,不易察覺,也難以治理”。但是我國具有量刑公正的制度保障,如果司法者能克服理念偏差,後續問題的化解也就不再畏難,後文也将對此詳論。
三.量刑情節在不同地區的适用差異檢測
在數據庫中,遼甯、江蘇、湖南、雲南的樣本總量均在 400 件以上,甘肅、河北的樣本總量也均在 150 件以上,樣本量能保障統計結果的有效性。各省最低宣告刑均為 6 個月,但最高刑差距較大,湖南和雲南為最高幅度之頂格(15 年 ),甘肅則為最高幅度之起點(10 年),江蘇、遼甯、河北居中(前兩者 12 年,後者 10 年 6 個月),表明宣告刑在整體上存在地區差。刑罰中值也存在地區差,江蘇和甘肅最重(36 個月),湖南和雲南次之(30 個月),遼甯和河北最輕(24 個月)。因而六省的宣告刑整體存在差異,下文對此假設予以具體檢測。
(一)宣告刑的整體地區差異
比較差異存在多種檢驗方法。采取 K-S 法對自由刑進行正态性檢測,發現其不呈正态分布,也不呈現方差齊的特征,因而法學界較多學者采用方差不齊時的 Tamhane's T2 方差檢驗法。但是統計學界主流學派認為“方差不齊不應采用方差分析,而應采用非參數檢驗法”。筆者對兩者予以實證比較并擇優運用。兩種檢測方法所得結果均表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宣告刑存在地區差異,但差異的具體樣态不同,用 Tamhane's T2 檢驗存在差異者,在非參數檢驗下也存在差異,但前者檢測不存在差異者卻可能為後者檢測出差異,從而說明前者誤差較大,後者精密度更高,故本文選擇非參數檢驗法,具體檢測結果見表 3-1。

根據檢測結果,河北與江蘇、雲南、甘肅,遼甯與江蘇、雲南、甘肅,湖南與雲南、甘肅,以及江蘇與雲南、甘肅的宣告刑之間均存在差異。而河北與遼甯、湖南,遼甯與湖南,湖南與江蘇,雲南與甘肅的宣告刑不存在顯著差異,從而說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量刑整體存在地區差異。
但此種差異并不直接表明各地區之間量刑标準不統一,也有可能為量刑情節本身差異所緻,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地區量刑差異中是否蘊含量刑情節适用不規範問題。限于篇幅,本文僅展現典型地區的檢測結果,但将對所有檢測結果概括列表,并将有關内容滲透在分析中。江蘇、遼甯和湖南三省樣本總量相對龐大,且絕對值相差不大,因而不需要加權處理,而且在複現邏輯中代表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因而取其為樣本比較适當。此外,隻有情節頻率夠大才具有統計學意義,根據統計,三省的立功和湖南的當庭認罪比率均低于 5%,從而無需評價。
(二)量刑情節适用具體地區差異
1.江蘇省量刑情節适用實況
根據研究目的及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性質,此處可采用線性回歸模型。在複現邏輯中,江蘇省經濟發達且司法人員素質較高、也是我國量刑規範化改革的前沿地區,其量刑質量應屬全國上乘,檢測結果(表 3-2)也證明确實如此。

根據模型摘要,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預防刑在宣告刑中占比 18.4%。在系數表中,P 值顯示,累犯、自首、坦白、認罪認罰、當庭認罪均發揮了量刑價值,隻有前科未對宣告刑産生影響。而根據 Beta 值,除了累犯與宣告刑正回歸,其他情節均為負回歸,因而回歸關系正常(從嚴情節會導緻宣告刑加重,從寬情節會導緻宣告刑降低)。具有回歸關系的量刑情節對宣告刑的影響力大小為:認罪認罰 >自首>坦白>累犯> 當庭認罪。從中可見,江蘇省認罪認罰的量刑作用顯著,各量刑情節運用較充分,量刑幅度掌控亦比較合理,隻有累犯從重幅度相對偏小。
2.湖南省量刑情節适用實況
根據湖南省的量刑情節回歸模型(表 3-3),湖南省預防刑在宣告刑中占比 6.1%,僅為江蘇省的三分之一,量刑情節适用不充分,特别是坦白、認罪認罰此類非常顯性的情節均未能發揮量刑價值。而根據 Beta 值,存在回歸關系的情節之影響力大小為,自首 > 累犯 > 前科,其中自首、累犯與自由刑的回歸關系正常,但前科與刑罰卻為負相關,即認定為前科反而會使刑罰降低。


應該說,司法者不可能将前科視為從輕情節,此情形可能是裁判文書撰寫不規範,未将具體案件的量刑情節充分載明所緻。不過這種量刑情節價值颠倒的情形在其他省份也存在,如河北和甘肅,說明應探索根源以從根本上消除。前科适用無效,甚至效果相反,說明量刑中存在遮蔽前科價值的其他事物。而在我國三階段量刑中,決定宣告刑者主要為起點刑與量刑情節,因而應于起點刑的設置及情節适用上尋找原因,在此,關于前科的性質和價值在認識上并無疑義,因而問題應在前者。如果起點刑設置偏離正常值明顯,即使适用量刑情節,最終刑罰也可能與不存在量刑情節但起點刑設置合理者未有差别,其結果便是量刑情節的假适用,甚至适用價值颠倒。例如,認定犯罪分子存在前科,但由于起點刑定位太低,即使對前科予以從重評估,最終宣告刑仍可能與其他無前科但起點刑合理的宣告刑無區分,甚至前者刑罰更低。因此,量刑情節的合理運用務必與合理的起點刑相配合,才能最終确保量刑情節對宣告刑發揮合理價值。那麼起點刑的設置應采取點的理論還是幅的理論?我國量刑指導意見采用幅的确定方式,在理論上則存在對立見解,有學者認為“點的理論與幅的理論相比較,點的理論比較可取,責任刑的點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與責任相适應的刑罰應該是确定的,否則對犯罪人的最終宣告刑也談不上是确定刑種和刑期”。筆者認為應區分規範與事實,規範具有普遍性,面對千差萬别的犯罪事實,規範上的刑罰隻有存在幅度才能方便司法者根據案件事實進行具體衡量;而作為具體個案,司法者需要根據具體犯罪事實在規範的幅度内确定具體的刑罰點,否則最終宣告刑會成為不定期刑,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簡言之,起點刑應采用幅的理論,且各省的設置幅度應大體相當,否則不僅起點刑因其自身差異可能招緻類案不類判,還可能通過損害量刑情節适用的規範化而導緻類案不類判風險增加。
3.遼甯省量刑情節适用實況
根據遼甯省量刑情節适用回歸模型(表 3-4),遼甯省的預防刑占宣告刑的 11.8%,較湖南高,較江蘇低。通過系數表可知,累犯、自首、坦白、認罪認罰、當庭認罪均與宣告自由刑存在回歸關系,隻有前科與宣告刑不存在回歸關系。根據 Beta 值,各種回歸關系正常,存在回歸關系的量刑情節對自由刑的作用力大小依次為,認罪認罰>自首>坦白>當庭認罪>累犯。由此可見,遼甯省對于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量刑情節适用水平與江蘇省相當,認罪認罰的量刑價值顯著,量刑情節适用較充分,幅度相對合理,但前科未發揮量刑效用,累犯從重幅度明顯偏不足。

綜上,江蘇省和遼甯省量刑情節适用較充分,認罪認罰量刑價值顯著,但前科未能運用,累犯從重幅度不足;而湖南省量刑情節适用不夠充分,認罪認罰的制度功能未能彰顯,但累犯從重幅度比較合理。在此,認罪認罰制度呈現帶動量刑情節運用合理和提高量刑質量的功能,認罪認罰的适用比率與量刑情節适用質量之間的正相關性在河北、雲南、甘肅的建模分析中同樣得以體現。
四.量刑情節适用差異問題解析
通過上文第二和第三部分實證檢測可得出如下結論:(1)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整體質量尚可。司法機關對于自首、坦白此類傳統量刑情節運用較規範,但酌定、從重量刑情節的規範化程度有待提高,因此進一步加強酌定及從重量刑情節适用有助于在該類案件中消除同案不同判風險。(2)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适用具體問題較嚴重。不同犯罪主體以及不同地區之間量刑情節适用充分性和适用幅度均差别較大,表明我國掃黑除惡犯罪量刑中存在标準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等背離我國量刑規範化改革目标和掃黑除惡常态化機制的不規範行為。(3)認罪認罰從寬的适用比率俨然為預防刑裁量質量的衡量标尺。凡是該制度運用比率高的省,量刑情節運用亦充分,幅度亦較合理,反之亦然。這一規律在 2018—2020 年的宣告刑與量刑情節适用的回歸模型中亦存在, 因此,除了肯定司法機關在探索量刑規範化路徑中取得的成就外,更需對其存在的問題或某些規律性邏輯進行深度解析,從而明确今後努力的方向。
累犯從重幅度不足需要從極端化用刑理念上展開深度思考。一方面,嚴重犯罪分子量刑中依然殘留重刑主義。嚴重犯罪的累犯量刑幅度在嚴打期間也存在适用缺陷,“嚴打”往往将嚴重刑事犯罪頂格判處,從而使得累犯的從重被閑置。自 2005 年我國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來,重刑主義思維不斷得以克服和消減,但在特别嚴重犯罪分子中仍有殘留,例如前述檢測得出包括累犯在内的量刑情節均對組織、領導者無意義,其刑罰幾乎完全由其組織、領導者的身份确定。另一方面,由于累犯從重的依據不明确,标準不統一,在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理念下, 司法實踐容易對較輕犯罪分子從嚴幅度不忍下手。有實證研究發現,“除了累犯後罪的性質與輕重和累犯從嚴幅度呈顯著正相關以外,累犯前罪的輕重與性質,累犯前後罪的關系,累犯前罪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以後至再犯罪時間的長短對于量刑結果均不産生顯著影響”。累犯從嚴依據單一正是從嚴幅度不足的直接原因。但是,必須重視補足累犯從嚴的幅度。有研究證明,“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的十多年間,美國犯罪率連續下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對一批累犯和慣犯判處了長刑”。我國也有學者主張,“對于部分具有更深的主觀惡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險性的累犯來說,從重處罰原則所産生的威懾力及适用所産生的刑罰量不足以起到懲罰和遏制犯罪的作用,因而應加重處罰”。
認罪認罰這種帶動量刑情節适用的規範化的價值可通過認罰制度的整合功能來解釋。因為量刑情節既然為功能性存在,其必定處于一定的價值脈絡體系中,從寬從嚴情節均并非孤立地發揮作用,例如自首中必然存在如實供述(坦白)的細節,成立自首者也不可能不當庭認罪。因此,量刑情節的系統化程度越高,情節沖突和競合的問題越少,從而越能促進量刑規範化。而認罰制度具有将零散的從寬情節予以系統化的功能,從而适用該制度能夠克服量刑情節分散可能導緻重複評價或評價不足等缺陷,增強量刑的規範性。因而如此一項好制度理應常态化運用于如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般嚴重的犯罪中。
然而,如果聚焦于簡單的因果邏輯,對于上述實證檢測出的問題将很容易解答,要建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适用的常态化機制嗎?去克服量刑情節适用的主體差異和地區差異;去規範酌定和從重量刑情節;去擴大認罪認罰制度的适用。但是這種解決路徑具有頭痛醫頭的弊端,而且此種克服、規範或擴大也非易事,它受制于量刑規範化的整體司法生态。即便是反對黑格爾的一元論者,也難以斷然否定其體系化的方法論,例如拉德布魯赫是康德二元論的忠實信徒,但其關于法律規範性質的著名三原則,安定性、合目的性、正義性就具有體系的思維。根據體系思維要求,精準定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适用常态化的目的是解決量刑差異的前提。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常态化懲治機制的目的何在?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努力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黨中央對司法的最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國量刑規範化改革也呈現出以公正價值為導向,推動實現同案同判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同案同判一直是近些年來我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因而掃黑除惡常态化機制下的量刑常态化也應以促進同案同判為價值導向。建立掃黑除惡常态化機制要求化解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中的主體差異和地區差異,這種差異的化解同樣應聚焦于推動、實現同案同判。不過,對同案同判的理解如果停留于“不同法官對同一法律的理解與認識可能存在偏差,導緻類似案件不能得到類似處理”, 那麼,這種依法辦案的層面,仍是法治主義的重申,仍無法凸顯其特定的時代内涵和價值。同案同判更應體現在這類特别案件——“裁量結果無法由理由完全決定,裁判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任意選擇,或者要在不可通約的價值間做選擇,又或者相關理由是不确定的(比如因為道德模糊性)”的裁量理念上。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恰屬此類特别案件,其量刑情節的獨特性很分明。根據前文統計,其累犯與前科并存率高,坦白率大,認罪認罰适用率極低等,如此極端的情節分布規律要實現“三個效果”統一甚為艱難,因而此類案件的同案同判更難以把握。如果将實現路徑僅寄托在規範酌定和從嚴量刑情節等立法技術層面,以及推進認罪認罰适用的司法制度層面,則難以保障規範或制度運行的長久效力,即使克服了此處量刑情節的适用偏差,這種偏差又可能在其他情節适用中出現。因為“在很多(而不僅是在若幹臨界)案件中,法官的價值判斷會取代立法者的價值判斷,對之亦無從依客觀标準做事後審查”。既然價值判斷對于規範法官、促進同案同判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中,轉變情節适用理念較提高情節适用技術也就更重要。
五.量刑情節适用常态化觀念的确立
前文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量刑情節适用的實證檢測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重罪量刑的普遍問題。目前我國學術界對重罪量刑的研究幾為空白,隻有少數實務界同仁重視重罪量刑的難題和偏差,并對重罪量刑情節的意義給予更高的評價,進而主張“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可以兩極化”。綜合上文分析,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為代表的重罪量刑存在的情節适用中的犯罪主體差異、地區差異以及認罪認罰适用率低等特殊問題,應樹立從寬量刑情節在犯罪主體中平等适用、認罪認罰制度在重罪中推廣适用的觀念;同時對于前文提及的預防刑情節認定标準形式化的普遍性問題應樹立判斷标準實質化的觀念。
(一)從寬量刑情節之于嚴重犯罪主體的适用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宣示嚴懲的犯罪,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主犯嚴懲的規定也遍及掃黑除惡的各法律文件中,那麼此嚴懲除責任刑差異顯著外,是否還應在預防刑的裁量上特别從嚴,甚至不适用從寬量刑情節?簡言之,從寬量刑情節是否适用于嚴重犯罪者。對此,盡管學界未見明确的否定,但暗示的否定之音卻較強烈。例如“僅是初級犯、偶犯和未成年人犯,受蒙蔽的、積極配合偵查的、提供犯罪線索的犯罪分子應當從寬”。該觀點耳熟能詳,且廣為接受。但仔細分析卻發現,其除了暗示從寬适用并無一般性标準外,還将嚴重犯罪分子排除在從寬的視野外。從寬不是量刑結果嗎?它不是取決于量刑情節嗎?如何能單純依據犯罪主體特征而确定從寬與否呢?
實際上,隻要肯定法治主義原則,從寬的一般适用标準就并非無法可依,而是應依照刑法規範和刑法精神來決定,否則罪刑法定原則即淪為空談。除了規範的視角,從寬還存在刑事政策的支持。是否考慮從寬,必須接受人身危險性标準的評判。無論在法治主義還是刑事政策的檢測下,除主體身份與刑事責任年齡存在直接關聯而為刑法明确規定為從寬情節外,犯罪主體身份均非當然的從寬量刑情節。而如初犯、偶犯,我國刑法總則無一般性從寬規定,分則也隻對部分特定犯罪作出規定。由此推斷,初犯和偶然并非一概從寬,如果犯罪主體表現出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在刑事政策上也排除從寬處罰。而且犯罪人隻可能或者是初偶犯,或者是前科累犯,法律規定對後者從嚴,如果對前者從寬,那麼寬嚴的參照者是誰呢?豈不意味着一個人犯罪或者從寬,或者從嚴,而無“正常”狀态。“無論是法定情節還是酌定情節,從寬情節還是從嚴情節,都有以什麼作為從寬或從嚴的基礎的問題。”總之,犯罪主體的身份與量刑從寬與否并無實質關系。此外,受蒙蔽者應從寬嗎?“受蒙蔽”此類術語很難進行規範化表達,如果其為受騙而犯罪者,則其根本就缺少犯罪故意,也很難存在過失,怎可能對一個不構成犯罪的人從寬呢?總之,單純以犯罪主體身份,而不考察犯罪主體身份所蘊含的人身危險性,就判斷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涉黑地位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不适用從寬量刑情節的觀念有失公允。
不僅如此,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具體刑事政策的變遷也證明此類嚴重犯罪者亦可适用從寬情節。如果說 2018 年 1 月 16 日“兩高兩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幹問題的指導意見》強調對組織、領導者絕對從嚴懲處,那麼 2018 年 2 月 2 日聯合發布《關于依法嚴厲打擊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的通告》已經具有為組織、領導者架設從寬處罰的黃金橋之意旨。2019 年 4 月 9 日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更是明确要求對組織、領導者貫徹總體從嚴的方針,特别是“兩高兩部”2019 年 10 月和 11 月聯合頒布的《關于跨省異地執行刑罰的黑惡勢力罪犯坦白檢舉構成自首立功若幹問題的意見》《關于敦促涉黑涉惡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擴張至所有涉黑涉惡犯罪者,這就意味着對組織或領導者也可以适用從寬情節。從中可見國家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組織、領導者從絕對從嚴,到鼓勵争取從寬,到相對從嚴,到明确可以從寬的刑事政策發展曆程,從而印證馬克昌先生所言,“即使是嚴重刑事犯罪,若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應予從寬判處;雖然罪行較輕,但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如累犯),則應依法從重處罰”。因此,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嚴懲并不意味着要将其中的主要犯罪分子“往死裡懲”,相反應以量刑事實為依據,依法依政策嚴懲。
司法實踐中的量刑情節适用主體偏見,可能誤導司法者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運用技巧聚焦至犯罪主體而非犯罪行為,從而對罪刑嚴重者忽視從寬情節,而對罪刑輕微者忽略從嚴情節,如此必定會導緻同案不同判。上文檢測結果證明量刑情節對組織、領導者無意義,對積極參與者作用較小正是此錯誤觀念的産物。在心理學上,該觀念可從近代人本主義開創者馬斯洛的疾呼中找到原因,“思考人的行為總是要圍繞人在希望着什麼”。犯罪發生時,人們容易對初犯、偶犯心懷惋惜并希望從輕發落,而對重刑犯憎恨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特别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重罪或重刑犯相遇時,此種偏見更加強烈。然而司法者需牢記,不帶個人偏見和喜好是其職業倫理的基本要求,“法律的宣誓完全可同希波克拉底的偉大誓言相媲美,……不對任何人帶有恐懼、喜好、友愛和酬報之心”。司法者不帶任何偏見應貫徹在整個司法過程中,特别是要堅持量刑情節适用主體平等原則。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于重罪案件的适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視為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有力的制度,然而即便支持重罪可以适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學者也容易對重罪中适用認罪認罰制度心存疑慮,因為适用認罪認罰的案件在操作上大多适用速裁或簡易程序,而重罪難以适用速裁程序,自然也就排斥該制度的适用。為此,此類含糊其詞的見解彌漫在學術界,“重罪案件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考慮如何從寬時,應注意區分案件性質,充分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确定是否從寬以及從寬幅度,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确保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此類觀點似乎在強調,重罪案件可以适用認罰制度,但從寬與否卻未必。但認罪認罰與從寬緊密相連,從寬是認罪認罰的适用後果,因而該觀點實質以責任刑(案件性質)為由否定重罪案件可以适用認罪認罰制度。對于責任刑與預防刑的關系,前者的内涵能否成為後者的适用條件,學界在責任刑的情節與預防刑的情節不能重複評價上已經達成共識,而這種以責任刑的情節為依據限制預防刑的适用之觀點即有重複評價之嫌。此外還有學者将認罪認罰與其他制度挂鈎而否定其适用于重罪,例如“被告人認罪認罰,但又無法得到被害人家屬的諒解,這樣的案件認罪認罰不但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實際上,“認罪認罰是犯罪人的事後行為,和犯罪本身的違法程度以及犯罪人在犯罪時的責任程度無涉,更主要的是同刑罰的預防功能相關聯”。難道重罪不需要預防嗎?馬克斯 • 韋伯曾雲,“任何公權力通常都包括懲罰的力量,不但直接以實力來去除不服從,并且更以不利于對方的威吓手段來令其屈服”。對重罪案件及嚴重的犯罪分子固然應嚴懲,但是也需牢記,“懲治效果必然局限在極有限的範圍”。較多犯罪行為難以借助懲治來實現正義,例如發生在家庭内、親人間的犯罪;也有較多犯罪難以通過懲治來恢複社會關系,特别是嚴重犯罪,更需要有效的預防政策。懲治需要以犯罪人的身體、财産或權利的損害為載體,因而實現手段很有限,難以與犯罪手段的無窮性成比例。因此重罪的用刑更需要考慮其預防功能,促進重刑犯認罪認罰使刑法功能十分經濟地實現。認罪認罰制度在重罪和罪刑犯中适用與輕罪或輕刑犯不應存在特殊性。
而且認罪認罰制度與普通程序也可以兼容,“認罪認罰從寬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過程,不受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制;适用于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普通程序存在實質化和簡化兩種操作方式,認罪認罰制度并非時下緩解辦案壓力的權宜之計,在重罪中,其可以通過普通程序簡化操作來實現,因而在我國未來刑事司法模式中存在廣泛的适用空間,“未來的刑事訴訟程序将區分為對抗型刑事訴訟模式和合作型刑事訴訟模式,前者适用以庭審實質化為基本要求的普通程序;後者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分别适用速裁、簡易、普通程序簡化審理程序”。我國更應推廣适用認罪認罰制度,自新中國以來,短暫适用的嚴打政策并不足以否定我國曆來、普遍性的刑事政策仍為寬嚴并存。如果說“國家—民族某時代的中心法理是該國家民族生存之基石,他們的一切法律、一切裁判均應以此為根據才能與客觀環境相适用,合符人民生活之要求”。認罪認罰制度正是一項契合我國人民司法本質、體現中國刑事司法特色的好制度。正是如此,我國《反有組織犯罪法》第 22 條确認,有組織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認罪認罰制度,因而有必要在重罪中對從寬量刑情節予以常态化運用。
(三)預防刑裁量情節判斷标準的實質化
如前所述,在量刑領域,同案不同判的根本問題在于量刑情節的适用不規範,而情節正确适用的前提是明确量刑情節的适用目的,如果為實現一般預防,則以行為為評價核心,若為特殊預防,則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為評價核心,隻有目的明确、一緻,才可能判斷标準一緻,進而推進同案同判。一般認為,量刑情節的适用貫徹特殊預防的意旨,如張明楷教授認為,裁量了責任刑之後,必須重點考慮犯罪人的再犯罪危險性,量刑階段的重點在于實現特殊預防。但是,當前司法機關對量刑情節的适用方式貫徹了特殊預防的理念嗎?雖然否定量刑具有特殊預防意義的觀點——“國家可以提出改造的目的,但不是向刑罰提出,而是對執行刑罰的機關提出”失之偏頗,但當前我國對預防刑情節的适用在實然上并未體現特殊預防理念。
我國司法實踐對前科等量刑情節的認定采取純規範的标準,例如累犯的成立需要具備罪質、罪刑和間隔時間等條件,自首的成立必須具備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的條件等。此類判斷均未與行為人的人格特征或人身危險性建立實質關聯,因而可謂形式标準。在此标準下,刑罰的效果很難對犯罪分子的人格矯治發揮作用,其量刑的個别化無非體現在裁量結果和裁量對象的因人而異上。但裁量結果的差異化在責任刑的裁量中也同樣存在,因為犯罪事實千差萬别,犯罪構成理論正是從萬千差别中提取的公因式,除此以外還存在影響犯罪構成要素的因素,其無法标準化,為此法定刑才采取幅的規定技巧。同樣,裁量對象的個别化也并非以犯罪分子個别化特征為實質依據,因為它未能體現刑罰是針對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而量身定制。實際上,當前采用特殊預防理論來解釋量刑情節适用的合理性也難以一以貫之。例如從重量刑情節的合理性基礎,有學者認為,此種情形并不是因為其人身危險性的緣由 , 而是因為先前的犯罪所引起的特定義務,即要求犯過罪的人在一定時間之内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 , 否則, 法律就要對其進行更嚴厲的遣責。可是除了禁止令,法律并無此類義務的一般規定,因而該主張違反了法治主義原則,而且否定了人身危險性或再犯危險性概念,特别預防又是預防什麼呢?這種否定人身危險性的立場反映了論者對人身危險性概念的“不信任”,正是如此,賦予人身危險性實質含義才是解決從重量刑情節的合理性根據,以及使預防刑情節彰顯特殊預防價值的根本所在。
在量刑情節認定的形式标準下,量刑情節與犯罪人之間隻存在形式關聯,而實際上卻與犯罪行為存在實質關聯。因為“隻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追問評價的效力才是有意義的”。既然不能孤立地評價犯罪行為,将犯罪行為置于犯罪行為發生前後的行為人情境進行綜合判斷就是合理且應該的,從而對前科等量刑情節的考慮實質是對犯罪行為的延伸評價,是基于犯罪行為發生前後的特定情境之考量。評價犯罪行為時應一并考慮犯罪行為的發生情境也許會被某些自由主義刑法論者指責違反了刑法保護法益之底線,擴大了刑法規制範圍。但“法益價值的減損隻能以實體性改變的方式得以體現,那就理解過于膚淺了”。犯罪行為固然可能直接損害法益,但懲罰從來都不僅針對實然、直接的法益損害結果,也包括可能的、間接的損害狀态,因而不僅是犯罪行為,對犯罪行為之前或之後的行為或狀态也應一并評價才能全面衡量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既然量刑情節與犯罪行為存在實質關聯,它就不可能擔負特殊預防功能,反而具有一般預防的屬性。
概言之,在特殊預防的理論中未能發現量刑情節的價值蹤影,而在犯罪行為的框架内将預防刑的裁量情節解釋為一般預防情節反而既有哲學依據,又符合刑法理論,但是這種解釋卻與當今新古典學派立場下量刑情節應然擔當特殊預防的功能不符,而且責任刑的裁量已經足夠體現一般預防,何須預防刑的裁量情節來加持呢?因而有必要将錯誤寄居在一般預防理論下的量刑情節遣回特殊預防的體系。遣回的路徑自然應回溯至問題的根源。既然導緻預防刑裁量情節價值錯位的“罪魁禍首”為量刑情節隻存在規範标準,而無人身危險性判斷的實質标準,那麼刑罰裁量中要實現特殊預防就必須對各種量刑情節的規範内容進行實質認定,在量刑情節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之間建立實質聯系,即對量刑情節采取形式和實質相結合的雙重認定标準。
如何确立量刑情節蘊含的人身危險性内容?盡管人身危險性的概念由實證學派提出,但該學派卻未能對量刑情節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建立科學可行的實質關聯,此也是招緻其被新古典學派取代的根本原因。實證學派受制于時代視野和方法的限制,其不能解決的問題在當今時代未必不能,新科技的發展,特别是大數據的運用已為解決此難題創造了前提條件。然而其非本文能夠解決,但是提示一些重大誤解也很有意義。例如“決定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狀況的因素應該包括犯罪前的一貫表現、犯罪過程中的犯罪事實以及犯罪後的悔罪态度”,此類宏觀認識并非人身危險性的判斷标準,而為人身危險性的判斷線索。又如“一個人犯了罪,不僅本人具有再犯可能,而且犯罪人作為一種犯罪源,對于其他人也會發生這種罪之感染”,這種基于過去假說符合概率邏輯,但用于特定個人則背離了近代自由刑法之底線,有違刑罰謙抑原則。總之,“特别預防論建立在行為人将來的犯罪這一展望性的刑罰觀之基礎上”。
由于預防刑的裁量情節的認定必須以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礎,但當前此類實證成果太少,根本無法為司法實踐提供量刑指導,因而司法機關隻能采取單一的規範标準。但是特殊預防的理念已經深入司法者的觀念中,既然單一标準存在量刑目标難以實現的遺憾,司法者即可能通過自由裁量予以矯正,為此裁判文書随處可見“盡管存在自首(或其他從寬情節),但不足以從輕”之類的無理之說理,使得量刑情節的存在流于形式而非價值存在,它意味着認可量刑情節,還不一定認可其量刑價值,如此矛盾或不确定性心理必然導緻類案不類判。但如果對量刑情節的規範含義能夠采取實質認定标準,能夠明确自首背後特定犯罪分子具有或不具有再犯的人身危險性,司法者對具有者從寬就不會有遲疑,反之對不具有者從嚴也會很堅決。因此除了在重罪案件中适用從寬量刑情節,特别是認罪認罰制度的常态化運用,對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進行确定性評價也是推進類案類判實現的強有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