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律評論》2022年第3期(總第5期)“學術專論“欄目

【作者】黎宏,法學博士,清華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教授。
【作者】丁文焯,清華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博士研究生。
【摘要】自動駕駛中“電車難題”式的碰撞選擇,是在所模拟的法益沖突發生時,對沖突中的個人法益的要保護程度之間的衡量,其實質是有關生命法益的緊急避險。盡管抽象的生命具有絕對價值,無法進行衡量,但根據具體的需要做出碰撞選擇的場合中不同主體所處位置不同,對于危險做出的承諾不同,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理應有所區别。因此基于對自主決定權的尊重,在一方做出承諾的場合,其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也相應降低,此時可以基于優越利益原則,選擇保全應受保護程度較高的生命法益。
【關鍵詞】自動駕駛;電車難題;碰撞選擇;緊急避險;允許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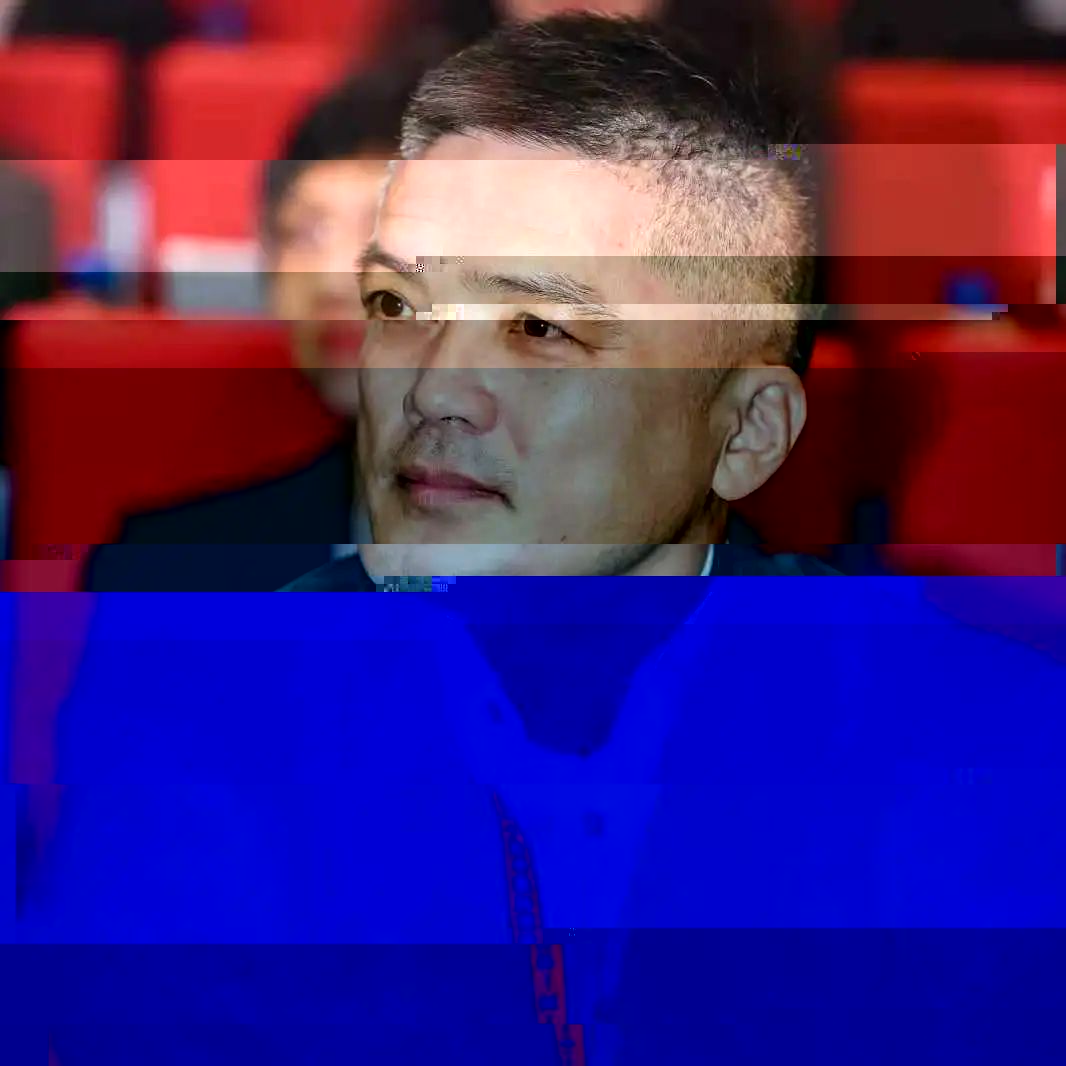
一、問題意識
自動駕駛的出現,為我們深化對刑法中的緊急避險制度的理解,提供了非常難得的具體适例。人能否犧牲他人生命來拯救自己,直接關系到緊急避險本身的法律性質與成立要件,包含生命能否被衡量的倫理考量,一直以來存在很大争議。先前,得因于并無亟須解決的現實難題,該問題大多依據教學案例進行假設推演,如“卡涅阿德斯之闆”,在不同場景中,行為人最終已經選擇了犧牲一方、保全另一方,之後再從裁判規範的角度,圍繞該行為是否成立緊急避險進行觀點展示。然而,如今自動駕駛汽車等級的提高,自動駕駛中遇到突發狀況時能否犧牲一方、保全另一方來進行緊急避險,需要在汽車投入使用之前就給出确切答案。
有關自動駕駛汽車的等級,目前市場中絕大部分車型為L1,即全部駕駛活動由人類駕駛員操控進行;小部分車型達到L2,即自動駕駛系統在駕駛活動中起到輔助作用,油門、刹車、方向盤等核心裝置仍由駕駛員主導;行業頭部已經實現了L3等級的核心部件量産,未來該等級的汽車在行駛時,系統會接管大部分駕駛操作,包括刹車、方向盤在内的核心裝置均由系統控制,隻有系統發出明确請求、給出一定反應時間後,駕駛員才會重新接管駕駛活動。這意味着L3等級汽車一旦投入使用,駕駛活動會在相當長的時間段脫離駕駛員的手動操作。此時間段中一旦出現突發狀況,不能同時保全在場所有人的生命法益,且無法請求駕駛員立即作出反應,就需要系統依據預先寫入的算法程序,自行作出犧牲哪一方、保全哪一方的碰撞選擇。例如,在類似“電車難題”的場合,一輛失控的大卡車迎面而來,系統必須瞬息作出選擇,是為了保全小型汽車内的乘員撞向道旁的無辜行人,還是不得犧牲無辜行人的生命,放任小汽車與貨車相撞(【案例1】)。這種碰撞選擇具有緊急避險的外觀,是自動駕駛系統程序中的一部分,在駕駛活動開始前已被提前寫入,而不是系統在突發狀況時基于自身意志當場作出。因此,在預先設置該程序時,需要明确何種碰撞選擇即便造成了損害結果,但從整體上看,該結果為刑法所接受。
目前,有關自動駕駛中與刑法相關的問題,我國理論界傾向于選擇允許危險路徑予以解決。該觀點認為,盡管現階段的自動駕駛技術尚未完善,難以避免引發交通事故,但該技術的發展從總體上看有益于社會,因此由系統或裝置故障引起事故的危險應當是允許危險。可以說,這是一種無關具體事故場合的、事前的宏觀考量。反觀碰撞選擇,如上所述,與駕駛活動中設計完備的系統發生預料之外的故障無關,是在系統運行之前的系統自身設計,是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具體場景進行模拟,判斷各種模拟場景下何種損害結果是能夠被允許的,從而依照該結果編寫出的相關算法程序,因此難以适用允許危險路徑。
對此,以下将通過對現有路徑的分析,來确定碰撞選擇問題的實質。繼而選擇違法阻卻事由之緊急避險路徑,結合緊急避險的正當化依據,與生命是否能夠被衡量的倫理考量,在厘清自動駕駛場合與傳統“電車難題”場合中的碰撞選擇有何異同之後,為自動駕駛具體場景中的碰撞選擇問題提供解決思路。
二、允許危險路徑述評
目前,有關允許危險在犯罪論體系中的位置,理論界存在不同見解:1.行為所實現的是法所允許的危險,不該當于構成要件;2.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但行為本身處于社會通常觀念所認可的範圍之内,因具有社會相當性而排除其違法性;3.行為本身遵守了行為規範,不存在注意義務違反,主觀上沒有過失。基于以上體系位置,對于自動駕駛中的碰撞問題,允許危險路徑也提出了三種思路,下文将通過對其逐一探讨,來厘清碰撞選擇問題的實質。
(一)行為性阻卻說之述評
行為性阻卻說基于客觀歸責理論,認為碰撞選擇程序的設計行為所制造的是法所允許的危險,因此可以直接在構成要件階段排除歸責。具體而言,該說認為自動駕駛系統與裝置的開發尚在起步階段,其運行過程必定存在隐患,同時也能夠為社會公衆帶來巨大便利。因此,基于社會整體性利益的考量,無論算法被設計為在突發狀況時作出何種碰撞選擇,該系統程序設計行為制造的都是法所允許的危險,不該當于構成要件行為。
然而,抽象的自動駕駛行為本身是否必然伴随發生法益侵害結果的危險,與具體場合中自動駕駛系統應當作出何種碰撞選擇,最終造成的損害結果能夠為刑法所接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前者有關某抽象出的行為本身是否通常伴随危險,後者則有關各種預設下具體場合的結果認定,不應将二者混淆,強行将允許危險法理嫁接于碰撞選擇問題之上。以目前交通活動中時常伴随的交通事故為參照,前者是指立法者雖然認識到駕駛汽車行為本身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危險,但由于該行為的實施能夠為社會生活帶來便利,因此在立法時允許遵守相關規範的駕駛行為,行為造成交通事故的,并不承擔刑事責任;後者則是指在具體的某次交通事故中,駕駛員為應對突發狀況需要當場作出選擇,何種情形下應當如何選擇,才能夠緻使損害結果不具違法,二者不可直接等同。
同時,在碰撞選擇中适用允許危險法理,是以行為的危險被允許為由,認為行為所造成的實害也被允許。推及自動駕駛場合,自動駕駛與目前的人類駕駛相似,其本身的運行必然伴随可能造成人員傷亡的抽象危險,該抽象危險基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而被允許,并不意味着當該抽象危險經過突發狀況下的碰撞選擇這一因果流程,最終現實化為結果時,該結果也必定被允許。如遵守規則駕駛汽車這一行為的抽象危險是被允許的,但這并不代表駕駛汽車遇到突發狀況,為了保全自己而撞死行人這一結果也是被允許的。從司法實務中的相關判決與不起訴決定書來看,對于後一種情形,司法機關也大多會考慮其是否成立緊急避險,而非自始認為遵守交規的駕車行為本身不該當于構成要件。因此,涉及自動駕駛中碰撞選擇的程序設計,就必然涉及具體情形中所作出各種選擇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之考量。此時不必再考慮抽象的行為本身,而是在具體的選擇行為造成了損害結果的情況下,來考慮是否存在具體的違法阻卻事由。
(二)違法阻卻說之述評
持違法阻卻說的學者認為,需要進行碰撞選擇的情形是極端罕見的,在其他大多數情況下,相較于普通駕駛員,自動駕駛擁有更先進的感知器,能夠快速在緊急情況下進行風險與利益分析,在駕駛活動中可能造成的傷害遠遠低于人類駕駛。因此,為了換取更大的社會善好而付出合理代價,對第三方生命法益施加的傷害應當是被允許。該說将允許危險作為一種具體的違法阻卻事由,基于優越利益原則,認為基于社會利益的考量,即使自動駕駛行為最終造成了損害結果,也應當肯定自動駕駛這一危險行為本身的正當性,因此着眼于重視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從而将對個人生命、身體法益的侵害予以正當化。
然而,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能否進行利益衡量,具體标準為何,目前仍然争議較大。依照允許危險理論,必須對該危險所帶來的社會利益進行必要性與有益性的判斷,即使認為該社會利益能夠優越于身體、生命的利益,也必須限定在實施了危險減少措施、且危險極低的場合,否則會忽視對生命法益的保護。目前,依照美國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最新公布的數據,從2021年7月到2022年5月,以并未出售上市的、運營商的測試車輛為對象,從其自身願意公布的數據上看,NHTSA收到了130起涉及配備自動駕駛系統的車輛事故報告。由此可見,當下的自動駕駛系統、裝置遠遠沒有達到所謂相較于人類駕駛的重大社會善好,所謂的能維護更為優越的利益,不過是制造商數據不透明下的自我營銷。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目前仍處于L3初期,在完全脫離駕駛員手動操作方面剛剛起步,可能造成的危險仍難以預測,若要在碰撞選擇問題上适用允許危險理論,隻有當自動汽車技術完備且全面普及,出現該問題的可能性極低的情況下,才存在認為其帶來的社會利益遠遠大于可能造成的人員傷亡結果的餘地,進而通過利益衡量來認定所有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皆不具有違法性。
同時,且不論社會法益與個人法益之間偏向社會法益這一價值判斷是否妥當,在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場合,存在的僅僅是個人法益之間的沖突,并不存在社會法益的相關考量。以【案例1】為例,此時的法益沖突存在于車外第三人與車内乘員之間,衡量的對象是無辜行人的生命法益與車内乘員的生命法益,需要進行的是個人法益之間的衡量,與自動駕駛技術所帶來的抽象的社會法益無關。而真正存在于交通活動領域中,需要在具體的社會法益與個人法益之間進行衡量的,是在尚未造成具體的損害結果,僅某一具體行為本身具有可能導緻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危險的場合,如醉酒開車送病人就醫是否構成緊急避險的問題。與之相對,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在車輛投入使用前已經被設計完備且寫入程序,選擇何種行為會造成何種結果已經被确定,這些損害結果是否具有違法性事關具體場景下生命、身體法益之間的衡量,與社會法益并無關聯。
(三)過失阻卻說之述評
持過失阻卻說的學者認為,若事先不能完全排除自動駕駛系統算法的偶然性結論,就不能要求算法編程人員具有注意義務。即使該偶然的算法結論引發事故并造成損害,隻要算法程序本身符合一般的技術安全要求,就不應該将罕見的損害結果歸責給上述人員。該觀點明确由于系統設定而造成具體損害結果的,責任主體應當是算法編程人員所代表的制造商,而不是駕駛室中的負有回應系統請求義務的駕駛員,或者是自動駕駛系統自身,這一點是妥當的。如上文所述,自動駕駛技術發展至L3時,包括方向盤在内的所有駕駛設備均由系統操縱,雖然其會在相關事宜上向駕駛員作出請求,但該請求僅限于路線規劃等可以提前作出、且駕駛員擁有充足時間予以回應的範圍。在此範圍外,遇到即将發生碰撞、必須當場作出選擇的突發狀況,無法期待駕駛員在極短的時間内得到并回應系統請求,此時作出選擇行為的隻能是系統本身。同時,自動駕駛系統有限的學習與選擇能力,是基于算法程序的預先設定,依據具體環境的不同,作出更多、更迅速、更貼切的反應,并不是系統本身擁有意志自由的體現。換言之,系統是基于算法程序作出的選擇,是算法程序的作出者,即編程人員的意志的延伸,隻是根據感應系統判斷此時處于哪一預先模拟的場景之中,進而作出相應的反應。其學習功能并不似人類的學習能力,會随着知識、經驗積累,調整或改變作出判斷的立場與相關考量,而是通過感應系統識别出更多場景,作出更為準确的判斷。在學習的過程中,系統作出判斷的立場與相關考量從未改變,依然源自最初寫入的算法本身。因此在自動駕駛的場合,責任主體理應是算法編程人員所代表的制造商,而非系統本身。
然而,該觀點之所以認為應當引入允許危險理論,來平衡自動駕駛技術風險與科技創新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因為“正如沒有完美的人,也不存在完美的系統,在享受自動駕駛技術帶來的技術優勢的同時,不能将該技術無法避免的罕見風險轉嫁給該技術的研發者、提供者”,即通過引入允許危險理論來限縮算法編程人員的注意義務範圍,從而“基于自動駕駛整體在安全性與社會利益方面的巨大技術優勢,而容忍兩難困境下的無法避免的損害”。但正如該觀點所述,允許危險理論解決的是“技術也無法避免的罕見風險”,是現有技術之外的風險,而碰撞選擇要解決的是現有技術本身如何設計的問題。以目前的人類駕駛作為參照,碰撞選擇無關刹車失靈這種現有技術難以解決的裝置瑕疵,而是制動裝置等一切設備完好時,正常駕駛活動中遇到突發狀況時的選擇。同樣的,允許危險理論可适用于系統本身運行故障,或是駕駛員本身存在失誤的場合,來解決行為所制造的危險是否超出了允許危險範疇,誰應當對超出部分擔責的問題;碰撞選擇則有關突發狀況時,駕駛員本身來不及接管、作出反應,正常運行的系統需要依照算法作出選擇,該算法在預先寫入階段已經明确何種選擇會造成何種損害結果,是具體損害結果間的利益衡量,與過失犯的成立與否無關。
三、緊急避險路徑之展開
(一)碰撞選擇的實質是有關生命的緊急避險
如上所述,現有的允許危險路徑,無論是基于客觀歸責還是社會相當性理論,其最終阻卻的究竟是行為性、違法性還是主觀過失,都是站在行為規範的角度,認為即使自動駕駛行為本身必然伴随着一定危險,但該危險行為總體來看有益于社會,因此為法所允許。然而,一方面,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無關抽象行為的自身性質,是在事先模拟的具體法益沖突的場合,明确各種選擇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再通過對處于沖突中的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性進行衡量,來考量選擇哪一行為造成的結果保全了應受保護性更高的法益,并不具有違法性。進而将導緻該結果的算法編寫為程序,使得适用該程序的自動駕駛系統在具體情形下作出相應的合法選擇。另一方面,與人類駕駛活動相比,相較于允許危險路徑,緊急避險路徑在結論上更為公平。人類駕駛員在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時,仍有可能被認為犧牲他人生命拯救自己不能成立緊急避險,系統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相關考量,卻直接被認為他人生命的犧牲是法所允許的危險,其實施的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行為不可罰,二者相較顯失公平。因此,有關碰撞選擇中生命法益之間的衡量,理應回歸緊急避險路徑進行探讨。
與“電車難題”相類似的,碰撞選擇在緊急避險路徑下讨論之所以困難,原因在于生命這一絕對法益是否能夠被衡量的争論。對此,需要考慮對生命法益進行衡量的緊急避險其本身的法性質、正當化依據以及其中倫理問題。同時,自動駕駛下碰撞選擇場合的避險人、被保護法益的主體與被避險人,與“電車難題”這一思想實驗的各個角色所對應的主體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在确定生命能否被衡量之後,需要通過兩種情形之間的比較,來确定不同場合中需要進行生命法益衡量的對象,以及在突發狀況下其各自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是否存在差異,從而對需要作出碰撞選擇的具體情形進行分析。
有關緊急避險本身的法性質雖然存在争論,但通常都認為以犧牲他人生命的方式進行的緊急避險,隻能阻卻責任。然而在自動駕駛的場合,如果認為碰撞選擇能夠成立緊急避險,該緊急避險的性質隻能是違法阻卻事由,而非責任阻卻事由。究其原因,是作為責任阻卻事由的緊急避險一般被認為依據的是期待可能性法理,即使造成了法益侵害結果,但考慮到行為當時的具體因素,無法期待行為人實施其他合法行為時,就不能對其施加非難,這意味着作為責任阻卻事由的緊急避險,其回避的僅僅限定于正在發生的針對自身法益的危險。而如上文所述,在法益沖突發生時,碰撞選擇中作出選擇的主體是駕駛系統本身,其回避的是正在發生的針對車内乘客或是直接碰撞對象的危險,且該選擇作為一種算法被提前寫入的,并非是在選擇時,即法益沖突發生時當場作出,不能适用期待可能性之法理。因此,有關此時碰撞選擇能否成立緊急避險之法律性質,也隻能限定于違法阻卻事由,并首先需要對作為違法阻卻事由的緊急避險本身的正當化依據進行讨論。
(二)碰撞選擇是生命的應受保護程度之間的衡量
1.應當以優越利益原則為正當化依據
關于阻卻違法性的緊急避險,一般認為其正當化依據是優越利益原則,即當所保護的利益大于或者等于所損害的利益時,肯定緊急避險的成立。在碰撞選擇中,即有關生命的緊急避險場合,有學者認為雖然生命具有最高價值,生命的質難以作出比較,但這并不意味着不能對生命進行量的比較,因此為了保全多數人生命而犧牲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被允許的。也有學者對此持否定态度,認為這是基于功利主義的考量,即強調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認為隻有行為或行為準則所導緻的結果對于所有相關人員追求更大的幸福而言是最佳選擇時,該行為或行為準則才是正當的,如果允許以犧牲個人利益來維護社會利益,就并未真正重視公民的個人權利。并在否定優越利益原則說的同時,提出以社會團結義務作為緊急避險和合法化的依據。
當然,優越利益說是基于功利主義的考量,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此處的功利主義并不是指如何使得社會法益最大化,而是指如何将處于具體的法益沖突之中的個人法益整體上實現最大化。如上所述,在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中,法益沖突是存在于個人利益之間的,與社會利益無關,無論是否允許對生命的緊急避險,都不會存在過于重視社會法益而忽視個人法益保護的情況。由此可見,作為緊急避險正當化依據之功利主義考量,與哲學或社會學上的功利主義内涵并不相同。功利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道德哲學而非利益哲學而誕生的,基本内涵是如果行為能夠讓最大多數人産生最大幸福,該行為就是道德的,而後衍生出了考量制定的政策、規則合理與否的判斷公式,即所有政策、規則的評價标準,就在于其是否指向了社會整體功利的最大化。因此,在社會法益與個人法益之間進行抉擇時,哲學意義上的功利主義的确更傾向于保護社會法益。與之相對,作為緊急避險正當化依據的優越利益,雖然的确部分采納了該“整體功利最大化”的公式,但該“整體”僅僅是處于沖突之中的個人法益的總和,而不是社會的整體。具體而言,緊急避險中的優越利益說是指,與遭到損害的利益相比,受到保護的利益得到了更高評價,從整體上看最終并未造成侵害法益的負面結果,其行為并不是值得刑罰處罰的行為。那麼在有關生命的緊急避險中,“整體利益最大化”指的是即使犧牲了一部分生命法益,但得到保全的生命法益能夠得到更高評價,從而整體上看使得所能保全的法益得到最大化。具體到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場合,是在不得不選擇犧牲一方、保全另一方的突發狀況時,能否認定一方的生命法益能夠得到更高評價,如何判斷哪一方的生命法益能夠得到更高評價的問題。因此,此時需要讨論的,主要是基于倫理學方面的考量,有關生命這一絕對最高法益能否進行質與量的衡量的問題,自始至終與社會法益無關。
此外,社會團結義務隻是換了一種考量邏輯,最終也不可避免地走入“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公式,依舊需要進行利益衡量。社會團結義務是基于羅爾斯的正義學說,以“無知之幕”為判斷前提,與“自私理性人”為判斷主體,以“最大最小原則”為判斷标準而展開的理論。具體而言,在思考某行為是否成立緊急避險時,需要預先假定所有社會成員都處于“無知之幕”之下,在“無知之幕”揭開前并不知曉自己所需要扮演的社會角色與所分配到的權利義務,且每個社會成員自身都是出于自私動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理性人”。因此,在緊急避險的規則制定之中,由于不知道在具體的緊急避險場合中,自己究竟屬于避險人還是無辜第三人的地位,隻能根據“最大最小原則”制定一個理性人都會認同的普遍規則,在緊急狀态中損害他人較小權益維護自己重大利益,同時承諾在他人重大利益遭遇危險時負擔一定的團結義務,對侵犯自身較小權益的避險行為加以容忍,從而與功利主義的社會決定相區别,在該問題上實現個人自主自決的“自我立法”。
然而,正如羅爾斯自己所說,相較于社會契約中的社會決定,正義論所提出的權利義務分配觀隻是更前置一步,并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具體的政府,而是為了提出一個抽象的一般性規則,從而體現社會成員的理性選擇。因此,當該一般性前置原則具象化,依據該原則來建立正當化政府與具體的憲法及其他規則時,實現的不再是一種個體正義,而是社會正義,這實際上依然是将自我決定轉化成了一種社會決定。在自動駕駛中的碰撞選擇場合下,“無知之幕”下的個體社會成員處于薛定谔的車内乘客與車外他人之間,或者說既是避險人又是被避險人,隻是要在二者之間不斷進行換位思考,此時其所要保全的最大法益和所要為他人犧牲的最小法益發生完全重合,即都是自己的生命法益。此時“最大最小原則”無法适用,但突發狀況之下必須作出選擇,使所要保全的生命和所要為他人犧牲的生命之間能夠“整體利益最大化”,這依然是有關生命法益是否能夠進行衡量的問題,即使此時在純粹假設的“無知之幕”下,沖突中的生命主體都是社會成員自身。
2.衡量的是生命的要保護程度,而不是生命法益本身
能否犧牲他人生命進行緊急避險這一議題之所以争議不斷,原因在于生命是一切其他法益的前提,擁有絕對的最高價值,應該被特殊保護。因此,即使是同意優越利益說的學者,也大多将生命法益作為常規的法益衡量之中的例外,認為任何人的生命都具有相同的價值,都享有同等程度的保護,不能将生命法益如其他法益那般進行量與質上的比較衡量,以犧牲他人生命為方式實施的避險行為本身依然具有違法性,隻能考慮以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為由阻卻責任。如果依照該觀點,在自動駕駛場合,系統本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方面的考量,犧牲一方的生命而保全另一方的生命而作出的碰撞選擇不能成立緊急避險。然而,生命法益作為絕對法益本身不可進行衡量,并不等同于具體場合中的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不能進行衡量;抽象的生命法益本身不能被标以砝碼,但碰撞選擇的具體場合中,為了使沖突中的法益回歸到平穩狀态,必須當場作出選擇,此時法益主體由于所處位置以及對于出現法益沖突所施加的原因力不同,其生命的應受保護程度可能存在差異。
上述持否定态度的觀點中,往往會以“人是目的”展開論述,該命題最初被康德闡釋為:“你要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人格中的人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時候都要将其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僅僅用作手段來使用。”即相比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該命題更确切的表述應該為“人性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有關此處“人性”的内涵,目前存在兩種理解,一是将其理解為廣義上的一般理性能力,二是要求更高一層次的道德理性能力。由此可見,“人是目的”這一命題中的“人”,并不是先于理性能力人前端的一種純粹的有生命的存在者,而是有生命、有理性且有道德的存在者。也就是說,“人是目的”這一命題所強調的并不僅僅是生命法益本身的至高無上性,而是基于生命法益之上的,對每個理性主體任意設定目的的能力,即對每個理性主體的選擇權利的尊重。那麼,在有關生命的緊急避險中,在考慮對于生命法益的特殊保護的同時,也應當考慮對于自主決定權的尊重,具體場合下作出了何種可能危及自身生命的選擇,應當在此時其生命的要保護程度上予以考量。也就是說,應當将生命的抽象絕對價值與生命具體的要保護程度相互區别。具體而言,盡管抽象的生命擁有絕對的最高價值,其本身無論在質或者量上都不能被用以比較衡量。但在具體場景下,如果一方實施了一定的行為,表明了對于可能侵害生命之危險的承諾,此時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行為人的自主決定權,考慮降低此時此刻的行為人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來對避險行為保護的生命法益與被避險人之間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進行衡量。
對此,也有觀點認為,重大身體法益與生命法益原則上無法通過被害人承諾阻卻違法,即使被避險人作出相應承諾,犧牲其生命進行緊急避險的行為仍不能構成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險。但不存在法益沖突時的承諾放棄是否有效,與存在法益沖突時,承諾一方的法益應受保護程度是否低于未承諾的一方,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如我國指導性案例中指出:“我國刑法沒有專門就被害人承諾問題進行規定,司法實踐中對有被害人承諾情形的故意殺人,原則上都不将被害人承諾作為殺人犯罪的阻卻事由,但可以作為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也就是說,存在被害人承諾的故意殺人,行為人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低于不存在被害人承諾的故意殺人。同樣的,依照日本刑法規定,沒有得到承諾的殺人罪與得到被害人承諾的同意殺人罪是兩個不同的犯罪類型,後者的法定刑要輕于前者。也就是說,放棄生命的承諾盡管不具有消除法益的要保護程度的效果,但具有降低生命的要保護程度的效果。因此,在法益沖突中,如果一方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了放棄自身生命法益的承諾,此時出于對其自主決定權的尊重,應當認為此時其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降低,與之相比,未作出承諾一方的生命法益應當受到更高程度保護。此時選擇犧牲作出承諾的被避險人的生命,保全未作出承諾的其他人的生命法益,應當被認為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險。
并未作出承諾的主體之生命法益,其應受保護程度依然是等同于絕對法益,應當受到絕對保護,不能進行量的衡量。而作出承諾的一方,其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降低,不再對其進行絕對保護的同時,也能夠對其進行量的衡量,如果雙方均作出同等承諾,那麼人數較多的一方應當得到優先保護。具體而言,在碰撞選擇的場合,哪怕撞向一個人可以拯救其他多個人的生命,但如果被碰撞方并未違反相關規範以及作出對侵害生命之危險的承諾,應當尊重其并不願意被犧牲的主觀意願,其生命此時依然具有最高價值,不能進行法益衡量,無法通過犧牲其生命的方式來進行緊急避險。以下,将對自動駕駛中碰撞選擇中的特殊問題展開分析,并讨論具體情形中應如何進行碰撞選擇。
(三)不同場景下碰撞選擇問題的具體分析
1.不同場景下要保護法益主體與被避險人的确定
對法益的要保護程度進行衡量,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在自動駕駛的碰撞選擇問題中,究竟何者是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何者是避險行為轉嫁危險後侵害的法益,以及雙方各指向哪一主體。雖然從外觀上看,自動駕駛的碰撞選擇問題與“電車難題”中的選擇問題極為相似,但無論是實施避險行為的避險人,要保護法益的主體,還是作為替代碰撞對象的被避險人,兩者并不總是相同。
如上所述,在“電車難題”中作出碰撞選擇的避險人是電車司機本身,行為保全的法益主體是五個并未遵守規則的人,而被避險人則是另一條道路上的無辜者。相對應的,在自動駕駛中,具有“司機”這一外觀的人類駕駛員并不是作出碰撞選擇的主體,真正在法益沖突中作出選擇的是預先設定好的系統程序。具體而言,L3及以上的自動駕駛系統在來不及向人類駕駛員發出請求的場合中,車艙内的所有人都是乘客,而乘客并不參與駕駛活動,對于法益沖突下的碰撞也無法作出選擇,真正作出選擇的是已經提前被寫入碰撞選擇算法的系統本身。該系統是算法編程人員基于制造商的要求,事先基于模拟出的具體情形,對所造成的損害結果進行衡量與選擇,從而編寫産生的。在法益沖突發生時,該系統充當了嚴格意義上的“電車難題”中的司機這一角色。原本的人類駕駛員的身份此時向乘員發生轉變,有些情形中是需要進行要保護程度衡量中的一方,有些情形中則類似“電車難題”裡的火車乘客,是與緊急避險行為所需要進行衡量的法益要保護程度無關的主體,以下對各類情形進行逐一展開。
首先,是人類駕駛員作為要保護程度衡量中一方的情形。在【案例1】中,此時的避險人是駕駛系統,或者說是駕駛系統背後的汽車制造商,要保護法益的主體是汽車上的乘員,被避險人是無辜的行人。此時作出的衡量,是基于相對超然的旁觀者視角,對艙内乘員與無辜行人之間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的衡量。可以說,相較于最初的“電車難題”,此時需要作出的選擇更類似于“9·11”事件中,究竟是否擊落飛機的選擇。即司機本身不再是作出選擇的避險人,而是作為交通工具艙内的乘客,成為要保護程度衡量中的一方,系統需要在其與無辜行人的生命之間作出選擇。此外,人類駕駛員的身份也有可能作為碰撞選擇之中的被避險人。如在來不及緊急制動的距離内,車輛行駛道路上突然出現一個或多個行人,或者自動駕駛的大型車輛遇到失控的小型車輛,此時轉向會導緻本車側翻,或沖出橋面從高處墜落,或撞向大型車輛或牆壁等危及車内司機的生命安全的場合(【案例2】)。此時是否要為了保護行人或小型車輛内乘員的生命而進行制動,同樣需要對其與本車人類駕駛員的生命要保護程度進行衡量。
其次,是人類駕駛員僅僅作為乘客,與要保護程度衡量無關的場合。如在來不及緊急制動的距離内,突然出現一個或多個行人,此時進行轉向雖然不會危及車内人員的生命安全,但勢必會撞向人行道上的普通行人(【案例3】)。這一碰撞選擇的場合則更類似于傳統的“電車難題”,隻是原本的避險人從司機變成了自動駕駛系統,原本的人類駕駛員則轉變為了無關的普通乘客,需要對生命的要保護程度進行衡量的,是與車内乘客無關的其他人。通過與“電車難題”的比較,可以看出在自動駕駛的碰撞選擇之中,需要衡量的法益主體從原本的雙方變為三方:直接碰撞者,轉向後的替代碰撞者,以及車内乘員本身。這三方在不同情形中身處位置不同,對法益沖突所施加的原因力不同,意味着其是否作出相應的默示承諾,同時又因為人數上的差異,使得是否能夠犧牲被避險人而緊急避險的判斷也各不相同。
2.具體場合中的判斷
首先,是車内乘員作為要保護法益主體,替代撞擊者作為被避險人,即【案例1】的場合。乘員作為自動駕駛這一技術便利的享有者,在接受自動駕駛所帶來的利益的同時,也對于自身可能遭受自動駕駛所必然伴随的抽象危險予以承諾。與之相對,作為被避險人的無辜行人,如果其遵守規範在道路兩旁行走,并未擅自闖入機動車道,未将自身生命法益置于危險境地,其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并未因其行為而降低,當駕駛本身的抽象危險在某一次緊急情況下現實化為具體結果時,乘員的生命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低于無辜的替代撞擊者。此外,如果作為被避險人的行人并未依照規範在人行道上行走,也實施了明知可能會導緻具體結果發生的危險行為,如闖入機動車道,此時雖然雙方都作出了承諾,但乘客作出的是對于自動駕駛活動可能伴随的抽象危險的承諾,行人作出的則是對此次可能發生具體侵害結果的危險的承諾,雙方的生命法益應受保護程度的降低也相應的存在差異,因此在對其應受保護程度作出衡量後,可以為了保全乘客的生命安全而選擇碰撞違反規範的行人。
其次,是車内乘員作為被避險人,直接撞擊者為要保護法益主體,即【案例2】的場合。一方面,如上所述,此時雙方皆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可能遭受的危險作出承諾,但承諾的對象并不相同,所以二者生命法益的要保護程度降低的程度存在差異,乘員的生命法益應當得到更高評價,得到優先保護;另一方面,此時的法益沖突現狀是由并未遵守規則的行人所創設的,可以說行人就是危險源本身,為了解決緊急狀況下的法益沖突,使法益重新回歸原本的平穩狀态,作為危險源的行人的生命的要保護程度,自然低于車内乘員的生命法益,為了保全車内乘員而選擇撞擊行人可以成立防禦性緊急避險,或者如果認為防衛的對象可以是過失行為,選擇對其撞擊的行為也可能成立正當防衛。
再次,是車内乘員并不是需要衡量的雙方,要保護法益的主體為直接撞擊者,被避險人為替代撞擊者,即【案例3】的場合。作為直接碰撞者的行人,對其違反規範的行為本身,與該行為可能導緻的對生命法益的損害是明知的,其基于自由意志實施了該行為,将内心層意思表露于外部,應當視為其作出了生命法益評價降低的承諾。此時不能為了保全其生命,選擇犧牲行走于人行橫道之上的,并未作出承諾的無辜行人的生命。即使此時行人本身走下了人行橫道,也存在對于可能危及自身危險的承諾,但由于此時直接撞擊者作為制造了法益沖突的危險源本身,為了消除法益沖突,其生命的應受保護程度在衡量時理應要低于不遵守規範的行人。
最後,是有關雙方人數對于碰撞選擇的影響。如上所述,隻有存在以行為作出對于危險的承諾,生命法益的要保護程度才會發生改變,從而不再受到絕對保護,才能夠被進行量的衡量。因此,如果僅有一方存在承諾,那麼即使承諾方在法益數量上大于未承諾方,也是鸷鳥累百,不如一鹗,不能選擇犧牲一個應受到絕對保護的價值對其進行保全。與之相反,如果雙方皆對危險本身作出了承諾,那麼此時雙方法益的應受保護程度均因其承諾而下降,因此可以基于量上的優越利益衡量,為保全人數多的一方而選擇碰撞替代人數較少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