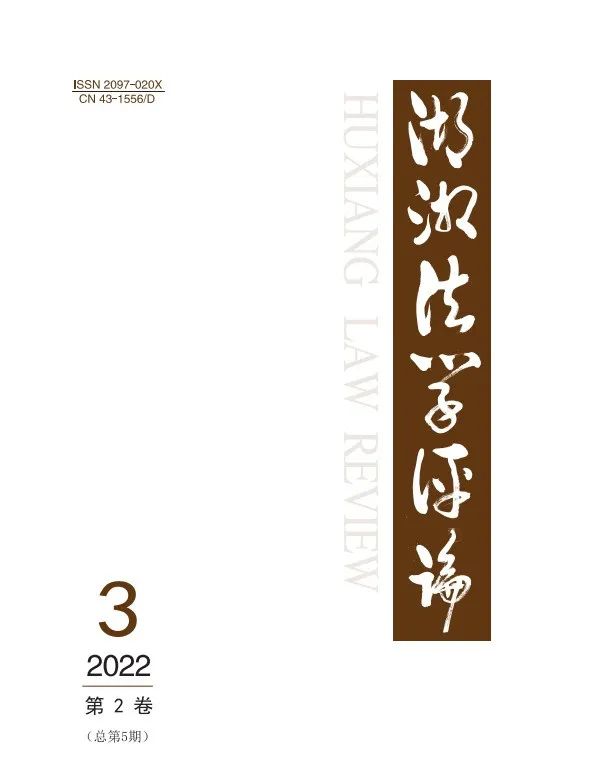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2年第3期(總第5期)“傳統文化與法治”欄目

【作者】俞榮根,西南政法大學退休教授,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摘要】《史記》和《漢書》所定義的“法家”,其治國之術為“尊主卑臣”“專任刑法”兩條,兩者均與法治相背。帝制中國欲緻治者所尚非“刑”、非“刑治”、非法家之治,而是“禮法之治”。現代法治非法家之治。
【關鍵詞】法家;法家之治;禮法之治;現代法治
公元 1999 年,新世紀到來的前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共和國治國史掀開了曆史性的新篇章。舉國上下,歡欣鼓舞。多年來,法學界貢獻了諸多關于現代法治“是什麼”的優秀著述,通過年複一年的普法教育,已然深入人心。拙文想換一個角度,說一下我們的現代法治“不是什麼”,那就是“現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一.法家與法家之治
諸子百家學派興盛于春秋戰國時期,至西漢得以系統整理總結。司馬談創“六家要旨”之說,東漢班固繼而論之,在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基礎上增縱橫、雜、農為“九流”,再加“小說”一家,成“九流十家”。感謝司馬氏父子和班固,用他們的如椽大筆,給世人留下了華夏文化史上百家争鳴、精彩紛呈的畫卷。如今,人們談論“六家”也好,評述“十家”也罷,其學術要旨為何,最接近真相的資料,莫過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藝文志》。畢竟,它們的作者去先秦不遠,且公認為史家之泰鬥。
何為法家?且看看《史記》《漢書》所論。
司馬談的“六家要旨”寫道: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司馬氏所論之“法家”,其特點有二:在治國方法上主張“嚴而少恩”“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在政治體制上主張“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明分職不得相逾越”。在司馬氏看來,後者是合理的,故“不可改矣”“百家弗能改也”。但“嚴而少恩”的治國方法弊端太多,“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班固在“九流十家”中對法家的概述,與司馬氏遙相呼應: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 ‘先王以明罰饬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對于“法家”那套“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的治國方法之弊端,班氏的分析和抨擊與司馬氏完全一緻。但不同之處在于,班固認為,那是“法家”中的“刻者為之”的結果。他特别指出:“法家”出自“理官”。秦漢“理官”中确有“刻者”與非刻者之别。“刻者”,正是秦之李斯、趙高,西漢甯成、張湯、王溫舒、杜周、趙禹等“酷吏”的形象寫照。
班固特别指出:“法家”出自“理官”。這一發現耐人尋味。班固揭示了“法家”含義中的刑事司法實務性特征。這應當歸功于他對秦漢刑事司法制度及其職官群體的觀察與考析。秦漢“理官”中确有“刻者”與“非刻者”之别。班氏“刻者為之”這一評斷,不僅指向治國方法上的學術主張,而且指向一種欲加之罪而刻意深求的刑事司法行為方式。班固的《藝文志》是一篇縱論“九流十家”的學術史力作。他所論之“法家”,盡管比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加重了刑事司法實務方面的分量,但仍然是學術法家、法家學派。
班固在《藝文志》中羅列的法家著作有:《李子》《商君》《申子》《處子》《慎子》《韓子》《遊棣子》《晁錯》《燕十事》《法家言》,計十家。千年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1982 年,中華書局開始編輯并陸續出版的《新編諸子集成》,在法家類中隻收了經後人校勘注釋過的《管子》《商君書》《韓非子》三大著作。1936 年,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在法家類著作中多收《慎子》一家。後人說到法家,大多指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韓非)之著作。如,明代人何良俊論法家雲: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
綜合司馬氏、班氏所論,“法家”一詞之本義,概要有三:
其一,“尊主卑臣”,君權至上。
其二,“專任刑法”“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
其三,以申不害、商鞅、韓非及其學說為代表。
這三條中,前兩條講的是法家的治國之術,第三條無關治國。
由此看來,法家之治,首推“尊主卑臣”,其次為“專任刑法”。班固認為,法家的“信賞必罰,以輔禮制”亦為“其所長也”。這是發司馬氏之所未發。“一斷于法”“信賞必罰”,用今天的話語表達,就是嚴格執法、執法必嚴,可以說是法家“以法治國”主張中的一抔精粹。此外,韓非的“法、勢、術”綜合為治之說,盡管與“尊主卑臣”多相重疊,但卻值得正面解析。下文打算從以上幾個切面展開法家之治,以圖說明它們為何不同于現代法治。
二.“尊主卑臣”的法家之治
古代政治家、史學家所津津樂道的“漢承秦制”,便是“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的帝制國體和專制政體。司馬談認為,這是諸子百家的共同認識,故“百家弗能改也”。為節約篇幅,就隻将儒法兩家來比照着說。
确實,儒家也是尊君的。孔子有“君君,臣臣”的說法。《禮記》載:“子雲:‘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但儒家尊君而不卑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之”,意思是犯顔直谏,實事求是,不拿那些虛假的莺歌燕舞來哄騙君主,欺世盜名。孔子向學生們劃了一道尊君紅線: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不能像那個昏聩的齊景公所理解的,隻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的意思,它還有一層“君要像個君,臣便像個臣”的含義。這猶如黑格爾的邏輯,在看起來保守的言詞中隐藏着革命的意義。
先秦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來得更直截,他痛快淋漓地指出: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一句話,君仁則臣忠,君不仁則臣不必義。他還認為: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意思很明白,盡管就政治統治上的職級(爵位)而論,作為君主的要高于臣子;然而就作為一個人的品德而言,為臣的可以高于君主。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荀子》書中有講君道、臣道的專篇,繼續闡發儒學的君臣論。其中很有創新的一處,是把臣民事君的情形分為四個檔次:大忠、次忠、下忠、國賊。
“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巳耳,國賊也。”
荀子怒斥的那些“偷合苟容”“持祿養交”的“國賊”,就是孔子所說的“欺之”之臣,他們用花言巧語搪塞、哄騙君主,為的是掩飾自己那一顆貪婪的私心。
綜觀儒家之君臣論,尊君而不卑臣,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以道合。這個道就是一個字:“仁”。“仁者愛人”“仁民愛物”。“仁”是國家的立國之本。國之為國,其基本價值體現為“民本”。儒家的“民本思想”為學界所認同,本文為論題和篇幅考量,不再展開讨論。質言之,儒家的尊君論,是一種理性的、相對的、民本位的君主主義。
回過頭來看看法家的“尊主卑臣”論。
君主“獨制”宸樞,乾綱“獨斷”的觀念,可能形成于申不害、商鞅那個時代。法家學說集大成者韓非在其書中曾引用申不害的“獨斷”論: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韓非在“獨視”“獨聽”“獨斷”之後,又加了三個“獨”:
“明君貴獨道之容。”
“(君主)獨制四海之内。”
“王者,獨行謂之王。”
“獨制”一詞,又見于《商君書》:
“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制獨斷于君則威。”
在君主“獨視”“獨聽”“獨斷”“獨道”“獨制”“獨行”的政體下,公卿百官、地方官員一切服從中央,聽命君主,其職責就是機械地做君主的馴服工具:守土牧民、搜刮民脂民膏上繳中央。這正是那套中央集權、皇帝擅斷的“秦制”。他們不能有自己的頭腦,不能有“私言”“私視”,順上唯上,無是無非:
“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
韓非還為之拟了十六字口訣: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對于君臣關系,韓非有句名言:
“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
在他看來,君臣之間隻是一種相互算計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關系: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
韓非告誡時君世主,儒家宣揚的那種“君禮臣忠”“君仁臣義”關系隻會弱國、亡國,隻有不仁不義才能稱王稱霸:
“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則可以王矣。”
但韓非隻創建學說,屬于理論家類型,立言而未能立功。韓非慕秦而西渡秦國,卻被他的同學李斯和另一個讒臣姚賈設計害死獄中。李斯成為法家學說在秦的真正推行人。坊間稱他為“法家實踐家”。法家的“尊主卑臣”怎麼樣,李斯在秦的實踐最有說服力。
據《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記載,李斯位居丞相之後,所做的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是堵塞言路,出台“以古非今者族”酷法。這一酷法是“焚書坑儒”的法律依據。商鞅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以古非今者族”及其結出的毒果“焚書坑儒”,便是李斯将“壹賞,壹刑,壹教”付諸治國實踐的新樣本。李斯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的理論根據是: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是徹頭徹尾的歪理邪說。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結果是:臣民悚懼,萬馬齊喑。李斯協助秦始皇建立了亘古未有的中央集權制度:皇帝絕對獨裁的君本位君主主義制度。
儒家、法家都持君主主義,這是司馬氏所謂的“不可改矣”“百家弗能改也”之處。然同中有異,儒家所持為相對的、民本位君主主義,法家所鐘乃絕對的、君本位君主主義。
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君主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然而,從學說而論,民本位的君主論還是比君本位的君主論來得理性一些、人民性一些、政治文明一些。
從治國方法上說,君主制政體下之治,有法律,有法制,但均在君主之下。言出法随、口含天憲,是君主制的常态。說什麼在帝制中國時代存在君主制下的“法治”,可能會把“法治”的标準降得太低,糟污了“法治”一詞,成為一種“話語腐敗”。
君主制勢必走向君權獨斷專制。秦政不啻是法家理論打造的君主獨裁政體之尤,李斯則是這一政制的設計師和操盤手。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這便是“法家之治”的總綱、要旨。若用現代治國理論分類,隻能劃歸徹頭徹尾的人治,而不是什麼法治。
太史公說法家的“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是“不可改矣”的治國綱領,明顯囿于時代局限。“漢承秦制”,帝制中國時期的曆朝曆代都“承秦制”,但帝制早已被中國人民送進了曆史博物館,那套“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法家之治,也同時在中國被抛進了曆史垃圾堆。
毋庸置疑,我們正在建設的現代法治絕不是那種“尊主卑臣”的“法家之治”。
三.“專任刑法”的法家之治
班固說法家主張“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堪稱确當之論。打開《商君書》《韓非子》,說到治國之術,反複論證的無非“以刑去刑”“以殺止殺”“嚴刑重罰”這些主張: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緻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
這是商鞅開出的治國藥方。他認為,隻要“行刑重輕”就可以“以刑去刑”。“行刑重輕”,就是對輕罪施加重刑。對此,韓非子很贊賞,并做了一番論證: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商代有一條刑法,棄灰于道斷其手。棄灰是輕罪,斷手是重刑,以重刑治輕罪,老百姓就不敢犯輕罪了。而像棄灰這樣的小過錯又很容易改正。于是,輕罪不敢犯了,大罪重罪也就不會發生了。
法家的這個藥方靈不靈呢?看看後來在大澤鄉發生的陳勝、吳廣起義就知道了。這是一群強征去築長城的農民,遇大雨而不可能按期趕到工地。秦刑法規定:誤期處死。他們一惦量,與其趕去送死,不如造反,拼老命一搏。誤期本是小過、輕罪,造反是一等一的重罪。人就一條命。既然誤期要處死,造反也不過是個死。何況,面前隻有造反或許是條生路,要是成功了呢?果然,大澤鄉義幟一舉,天下響應,秦王朝大廈瞬間倒塌。“輕罪重刑”之策,帶來的不但不是“國治”,而是國滅。
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韓非深谙老子的學說,怎麼就沒有悟透這一條!看來還是過分迷信君主的絕對權勢限制了他的認知。
“重重而輕輕”,意為犯重罪處重刑,犯輕罪處輕刑。商鞅、韓非認為,這樣用刑,會緻犯罪滋生,“以刑緻刑”,不能維持統治大局穩定,導緻國内生亂,國力削弱。這些話明顯是與儒家的刑罰觀相對抗的。儒家主張“罪刑相應”。如荀子說:
“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
“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
現代刑事法治理論中的主要原則之一,是罪刑相當,即“重重而輕輕”。毋庸置疑,法家“輕罪重刑”顯然背離了法治原則。
法家認為,制服臣民就靠兩手:賞和罰。用現在話語,叫作“胡蘿蔔加大棒”。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
但“賞”不是真賞,賞要少要輕,罰要多要重。他們說得很露骨。商鞅說:
“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
商鞅這一賞罰觀,韓非舉雙手贊成,幾乎抄作業一樣抄錄下來: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商鞅宣稱,國勢強弱決定于刑賞之間的比例:
“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
你想要稱王嗎?那就得“刑九賞一”。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可憐的隻占十分之一的“賞”,賞的是什麼?太史公對“商鞅變法”中的賞和罰有段精到的叙述: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緻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歸結起來,就是賞告奸、獎勵耕戰,重刑不告奸者、重罰經商等末利及所謂懶而貧窮者。怎麼判定是否有奸不告?或誰在從事末利?誰懶惰?商鞅的辦法很絕:制定連坐法。有什伍連坐、職務連坐等等。
韓非對商鞅的連坐法、賞告奸仍然無保留地站隊支持:
“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私奸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
“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
連坐法、賞告奸,乃是世間最陰險的惡法。它把全國變成一個大監獄,相互監督,相互傷害,相互絞殺,罰及無辜,更甚于“重刑輕罪”。其危害慘烈且久遠,不光髒了水體,更是污了水源。
韓非說:“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從漢初陸賈、賈誼的著作中,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可知韓非此言不虛。秦始皇之治秦,依然用的“輕罪重刑”“連坐”“告奸”等嚴刑峻法。他“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樂以刑殺為威”。那個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就用的告奸之法:
“于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谪徙邊。”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刑訊逼供,獎賞告奸,古往今來,制造了多少人間冤獄!
曆史的教訓豈能忘記!現代法治絕不能接受法家主張、秦代施行的“輕罪重刑”“刑九賞一”“連坐”“告奸”等“專任刑法”之治。
四.“法、勢、術”的法家之治
早期法家中有重“法”的商鞅、擅“勢”的慎到、用“術”的申不害。韓非認為他們都對,但都有欠缺。他集其大成,創“法、勢、術”綜合為用的新學說體系。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請特别注意“皆帝王之具也”這一對“法”與“術”定位并定性的結論。在韓非為帝王謀劃的強國治國體系中,“法”和“術”隻是帝王制馭臣民的工具、手段。其中,“法”是顯的,叫“明法”,“術”是隐的,稱“陰術”。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衆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
有論者以為,在韓非那裡,法、勢、術三者,以法為主、為本。其立論根據是:
“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
這裡的“法為本”,對應的是“道為常”,不是拿法與勢、術進行比較,不存在論定法、勢、術三者孰為本孰為末的語境。
韓非的“法為本”,“本”什麼?得從“道為常”求解。“道”這個概念,是韓非從《老子》那裡學來的。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
“道”,在《老子》那裡,本義是萬物之成其為萬物的固有規律。韓非在釋讀“有國之母”時,将“道”說成是治國之術。什麼是“常”?韓非說:
“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合而言之,韓非所要說明的“道為常”,是指即便“天地消散”也“不死不衰”的“有國之術”。它就是“法”的不變之“本”。這個“術”、這個“本”的具體含義,韓非有相當直白的表達: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
說來說去,還是以“明法”“陰術”整治臣下。請注意緊随“以法為本”之後的話:“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誰的“名”?君主是也。“法為本”則君主“尊”。“法為本”之“本”,“本”在“尊主卑臣”上,“本”在“明君無為于上,君臣竦懼乎下”。
君主如何才能把控好“法”與“術”兩個馭臣役民的治國之具?這就又回到前邊說過的“獨斷”“獨制”那六個“獨”上。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
實現“尊主卑臣”的奧妙,就在這個“勢”上。這威勢之“勢”,是至高無上之權力運作中産生的權力場效應,是一種通過持續威懾而生成對權力恐懼的勢能。這樣的權力場、權力勢能一旦形成,一國臣民無逃于君主威勢之下。韓非引慎到之言說明“勢”的重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霁,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诎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韓非在自己的著作中,反複強調,君主必須獨擅權勢,才能用“陰術”馭臣,以“明法”嚴刑治臣治民。反過來,君主又必須持續不懈地操“術”行“法”,才能保持和鞏固權勢。
在韓非的政治邏輯中,法、勢、術三者之間,構成一個君主治國之環,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其中,權勢是打頭的,是本、是主、是根。權勢是個“1”,其他都是“0”。對君主來說,無權勢,失權勢,一切免談,萬事皆休。
韓非這種君主一人獨擅權勢,操“陰術”,用“明法”嚴刑馭臣治民的“法家之治”,離現代法治不知幾千裡之遙矣。
五.“以法治國”的法家之治
法家思想中最令人贊許的應該是“以法治國”主張:
“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争。刑過不辟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上文已經反複申述,法家之治是一個君主擅勢、操術、用法的系統,其用法以“重刑輕罪”“連坐”“告奸”為務,對于“以法治國”,不應從這個系統中摘取出來孤立地理解和評述。這一點,商鞅、韓非自己都有闡述。如,君主應“秉權”而“垂法”:
“秉權而立,垂法而治。”
其“刑無等級”之“刑”,乃“重刑”“重罰”“連坐”之刑: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将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
“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緻霸王之功。”
故爾,“以法治國”不同于我們追求的“法治”。形似而質相異。
誠然,将其從君主“獨斷”“獨制”的系統中剝離出來,去粗取精,撷其英華,古為今用,進而啟迪新知,則完全應當,也可能。
我們撇開“惡法非法”還是“惡法亦法”的是非之争,來發掘法家“以法治國”主張中所蘊涵的積極元素,最恰當的概括,可以用“執法必嚴”,或“嚴格執法”四字言之。
這裡又要回到太史公對法家的定義和評價上去。他肯許“尊主卑臣”這一條,認為是“百家弗能改也”。其實,嚴格執法、“一斷于法”,也是百家所認同的。
還是以儒家為例。
史載,孔子稱贊晉叔向“治國制刑,不隐于親”,譽之為“古之遺直”。這說明孔子主張秉公執法、不徇私情。孔子曾為魯司寇,執掌司法大權。漢代董仲舒在書中這樣描述孔子的司法業績:
“至清廉平,路遺不受,請竭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
叔向乃晉國上大夫,身為貴族,堅守司法直道。孔子稱許叔向,自己為魯司寇時躬身踐行。“不隐于親”“據法聽訟”,就是嚴格執法。可見,法家的“一斷于法”,源遠流長,并非憑空而生。嚴格執法,是統治集團維系統治合法性的必須之舉,為儒家、法家所共識,隻是漢語遣詞造句的表達方法有所不同。法家用詞峻急,猶如戰狼之冷厲。
秦漢以後,刑事法律逐漸轉向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史稱“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領域,形成各級法吏嚴格以律斷案,大案、疑案或律所不及之案,則上報中央,交由法司機關首長,乃至六部、九卿大臣集議,最後報皇帝裁斷。這一帝制時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論表述首見于《晉書 •刑法志》:
“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滞;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于是,嚴格執法、“以律斷罪”成為帝國各級法史必奉的原則。在古代文獻中,這些法史常被稱為“法家”。刑律中有“不直罪”“失刑罪”等,專為懲治違律枉法、出入人罪的法吏。
綜上,法家“以法治國”命題中蘊涵着合理而有正面價值的元素,其嚴格執法這一原則最為法家所強調,也是儒家的共識,在帝國時代更是制度化為奉法官吏的職守要旨。不過,“以法治國”仍然是君主“獨斷”體制中以權勢統法術的一個環節,不能抽取出來拔高為“法治”思想。
六.秦漢以後諱言法家之治
前文說到,秦王朝短命而亡,但“漢承秦制”,秦制猶存。那麼,漢及漢以後的帝制王朝除了繼承“尊主卑臣”之中央集權、皇帝制度外,是否也承用秦代在刑事司法領域的法家之治呢?
為此,筆者搜索了古籍電子版文獻中的“法家”一詞,并逐條考察其詞義。
在先秦文獻中,現有電子版文獻中僅《孟子》有“法家拂士”一說,意為堅守先王禮法制度又敢于诤谏輔拂的賢能忠勤之士。《孟子》成書在秦漢之前,不入本文統計範圍。
秦漢之後的電子版文獻,以《四庫全書》古籍為主,輔以《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序跋選輯》一書所收序跋文獻。後者大多為四庫所未收。
在四庫古籍電子版文獻中,連同《史記》《漢書》在内,統共搜到出現“法家”詞條 71 處,“法家”一詞(含個别“法律家”“名法家”“刑法家”等)83 處,其詞義大緻可歸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指法家學派。即同《史記》《漢書》所言“法家”之義,計 16 處。其中,《史記》《漢書》中“法家”一詞 4 處,指原始法家。作為參照系,應該減去,剩下為 12 處。察其所論,有辨某書是否為法家著作者,亦有舉某人當為“法家”者。
第二類,其義為“刑名學”“刑幕學”。這不同于《史記》《漢書》所論之先秦原始法家,而是以儒學為筋骨的刑事法律學說,即古代之律學、刑幕學。誠然,這儒學,是經過漢以後曆代大儒改鑄創新而為帝制統治階層奉為主體意識形态的新儒學,但不失仁恕之本。其中,刑名學 9 處,刑幕學 4 處,共 13 處。
第三類,理官和典獄之官的代稱。他們都是執掌刑事立法、釋法、司法大權的帝國法務大臣、法曹官吏。“理官”一詞源自班固的“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典獄之官”取自宋呂袓謙“後世多以典獄為法家賤士”之說。諸如漢代廷尉及禦史大夫、隋唐“三法司”、明清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部院大臣等歸為“理官”,計 17 處,其他中央和地方審訊斷獄的刑獄官吏等劃入“典獄之官”,有 37 處。兩者相加共 54 處。
這一類“法家”有褒義的、有中性的,也包含貶義的。被貶稱的“法家”指酷吏和刻剝嚴刑之人。如《宋元學案 • 元城學案》記載宋代永州提刑官劉芮生平事迹:
“劉芮,字子駒,東平人也,……其為永州獄掾,與太守争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遂以疾求去。”
劉芮口中之“今世法家”,即為“生中求死”之酷吏。
又如,唐代元澹“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這裡的“不樂法家”之“法家”一詞,顯系貶稱。
《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序跋選輯》共收 213 種古代法律文獻的序跋,從中搜檢出有“法家”一詞的 34 篇,“法家”一詞計 42 處(含“名法家”等)。這 34 篇中,與四庫古籍中重複的有兩篇。一是元代柳赟的《唐律疏義序》,二是清末沈家本的《重刻唐律疏議序》。其餘都是前述的四庫古籍電子版中所未見的。
序跋中 42 處“法家”詞彙中,經分類,屬于“學派”詞義的 5 處,可歸入“刑名學、刑幕學(含司法檢驗學)”的 22 處,其餘 15 處意為“典獄之官、刑名幕友”等法務人員,其中多處為指稱司法檢驗人,即古代的“仵作”,今世之“法醫”。與四庫古籍重複的那兩篇中,各出現“法家”1 處,計 2 處,詞義均為“典獄之官”。因而這 15 處應減去 2,實為 13 處。
将上述兩處古籍所得“法家”詞義數據統合如表 1:

在四庫古籍電子版和古代法律文獻序跋電子版中,共搜索得“法家”一詞 123 個。除去《史記》《漢書》中作為“彼法家”的 4 個,餘為 119 個。它們的詞義析分為三大類:學派、刑名學等、理官和典獄之官等。現将這三類“法家”詞義作一分述。
首先,作為先秦諸子百家“學派”之一的“法家”詞義,有 17 處。考其原文,一為重述《史記》《漢書》的六家之論和九流十家之說,多出現在四庫古籍的“史部”《藝文志》《經籍志》,及一些學術史著作中,屬于介紹或複述司馬氏、班氏之說。二為指名道姓地說明是韓非、李斯等法家人物的學說、主張。總之,可歸入“學派”義的“法家”一詞,相當于英語、俄語等語言中的“過去時”,不是“現在時”,是曆史範疇,非當世學派。即是說,它們所指稱的均為學術史上的法家學說或法家人物。
其次,作為刑名學的“法家”學說詞義。這是先秦法家學說的 2.0 版。我們現今稱之為律學、刑幕學、司法檢驗學和法醫學等統統涵蓋于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家類”按語中寫道:
“刑名之學,起于周季,其術為聖世所不取。……至于凝、蒙所編,闡明疑獄;桂、吳所錄,矜慎祥刑。并義取持平,道資弼教,雖類從而錄,均隸法家。然立議不同,用心各異,于虞廷欽恤,亦屬有裨。是以仍準舊史,錄此一家焉。”
“凝、蒙所編”,指和凝、和㠓父子相繼編撰的《疑獄集》。“桂、吳所錄”,指桂萬榮、吳讷相續撰寫的《棠陰比事》。四庫館臣們把這些研究刑名法術的作品歸入“法家類”,又做了明确的區别。它們雖“均隸法家”,那隻是“仍準舊史”“類從而錄”而已。這些刑名學著作“義取持平,道資弼教”,與商、韓的學說“立議不同,用心各異”。
可見,這些“類從而錄”的所謂“法家”著作,顯然異于原始法家,是法家的新版本,是改進版。所謂“義取持平”“立議不同”,其實就是接納了儒家仁義中平思想,主張“祥刑”“慎刑”“恤刑”的儒家化刑名法術之學。
最後,理官、典獄之官等法曹職官,以及刑幕師爺、司法檢驗人員(仵作)等刑事法律參與人,稱他們為“法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法家類”提要中不曾說到的,恰是出現最多、最常用的“法家”詞義,有 67 處,占比 54%。此乃“法家”一詞的新義。最能表達這一新義的名詞便是“典獄”二字。
“典獄”之說為宋儒呂祖謙首創,明代丘濬在其名著《大學衍義補》中深表贊同,并大段摘引:
“(呂祖謙)又曰:‘典獄之官,民之死生系焉,須是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謂至公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複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典獄為法家賤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
呂祖謙指出,“典獄之官”應當“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這才是“至公無私”的“法家”。否則,便是“法家賤士”,即史家所斥之“酷吏”。
此“法家”新義,多為中性詞彙,亦可褒可貶。用現行的話語表達,此“法家”,即法律人,主要指刑事法律人。或反過來說,凡刑事法律人均可稱之謂“法家”。在這裡,“法家”隻是一個刑事部門官員和從事刑事工作者的職業名稱。此“法家”之“家”,既非諸子百家之“家”,也不是刑名法術學家之“家”,而與“史家”“詞家”“作家”“醫家”“商家”“船家”“東家”之類詞語的“家”相同義,是個職業稱謂。
“窺一斑而知全豹”。對古籍中“法家”一詞的詞義考析,可以促進我們反思古代中國政治史法律史的一些“全豹”問題。
先秦儒學曆經西漢董仲舒改鑄、宋明時期程(程颢、程頤)朱(朱熹)和陸(陸九淵)王(王陽明)創新發展,一直占據中國古代思想的主流地位,奉為正統意識形态。“法家”詞義的變化,說明先秦法家學說已為這一主流或正統思想所吸收融合,成為其組成部分。這從一個側面證明,“十年動亂”中編造的“儒法鬥争史”,以及“法家法治與儒家人治鬥争貫穿兩千多年”的“主線說”,隻是一部僞史,一種無根之妄論。
從古籍中所得的 123 個“法家”詞彙表明,“評法批儒”運動中所策封的“法家人物”,如王充、王安石、張居正、黃宗羲等等,沒有一個自诩或被同時代人贊譽為“法家”。我們既沒有看到哪朝哪代有哪一個主持修律、主政王朝法司部門的“理官”自诩為商、韓那樣的“法家”,也沒有看到他們有一字宣稱自己在總體的治國方略上是依照商、韓的法家理論來修律、主政的。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那些有作為的法司主官、典獄職官以“不樂法家”為榮,那些刑名法術之著述竟相标榜仁恕中平、“罪刑相當”“慎刑”“恤刑”之獄訟觀念,而不是商、韓的“重刑輕罪”“以刑去刑”“以殺止殺”這些狠話、酷法。他們羞與法家為伍,諱言“法家之治”。
七.古賢尚“禮法之治”而非“法家之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史部《政書類》“法令之屬”對《唐律疏議》等“法令”案語中有句名言:
“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
就是說,唐律等律典隻是“刑”而已,即今之“刑法典”。“盛世”不廢“刑”,但不尚“刑治”。“刑治”,就是法家之治。帝制統治者羞與商、韓為伍,諱言法家之治,那麼,他們所“尚”者何?這就需要追尋中國古代法的演進史。
長期以來,我們将中國古代法歸結為“律令體制”,也以此為基點論說中華法系。中國古代法有律令是事實,将律令視為中國古代法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沒有錯。但若說中國古代法、中華法系就是“律令法”“律令體制”,那就以偏概全了。
“三代”之時,夏有“夏禮”“禹刑”;商有“殷禮”“湯刑”;周有“周禮”“九刑”。那是一個“禮—刑”結構體制,其特點是禮外無法,法在禮中,出禮入刑。
春秋戰國,禮壞樂崩,“刑”掙脫“禮”而一端獨大,造極于嬴秦,形成“專任刑法”的秦制。這也是“律令法”發轫時期。秦代奉行“重刑輕罪”“以刑去刑”的“法家之治”,結果二世而亡。刑“為盛世所不尚”,正是“秦鑒”之真谛。
漢承秦制,又要免蹈秦之複轍。于是在法制領域向“禮”回歸。曆經五六百年的曲折反複,終于在魏晉有了“引禮入法(律)”的刑律典──魏《新律》和晉《泰始律》,至隋唐而大備。史稱《唐律疏議》“一準乎禮”。這便是我們中國法律史教科書中講的“禮法結合”。這裡的“法”,主要是“律”,即刑事法典。準确地表述,“禮法結合”,應為“禮律結合”。“律”便是“律令法”的主體。
漢代向“禮”的回歸,除“引禮入律”外,還有“律外之禮”這一更重要的面向。它又分走兩條路徑,一是制定廟堂“禮典”,二是倡導民間禮俗習慣法。兩者都是“律令法”無法包容的。
帝制時代的第一部“禮典”制定于西晉,取名《新禮》,與刑法典《泰始律》一起頒行于泰始年間,标志着“禮—律”結構的新型法律體制開始形成。進至唐代,《永徽律疏》和《大唐開元禮》雙璧同輝,“禮—律”體制的主架由是定鼎,成為宋、明、清“禮典”“律典”之圭臬,其特點是以禮率律,律外有禮,禮律互輔。
古代社會秩序的維系,僅靠“禮典”和“律典”自上至下的“禮─律”之治是遠遠不夠的,在相當程度上得助于民間“自治”。
古代社會的“自治”受“禮—律”體制保障,主要依據于禮俗習慣法。正是這些禮俗習慣法,使禮義紮根于社會土壤,滲入百姓心田,成為一種信仰,成為一種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識,并一代代口耳相傳,在生活中反複訓練,人們都能清楚地知道,依據自己的身份、年齡、性别,應該怎樣視、聽、言、動,也都能預計得到自己行為的後果。人的社會化就是禮俗化。這是一種在空間上全覆蓋、在時間上全充盈的規範群,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無法之法”。
這種由禮典、律典、禮俗習慣法組成的古代法律體系,名曰“禮法”。
被學界譽為翻譯亞裡士多德著作“第一人”的吳壽彭先生 ,在比較中西法律後指出:
“在近代已經高度分化的文字中實際上再沒有那麼廣泛的名詞可概括‘法律’‘制度’‘禮儀’和‘習俗’四項内容;但在中國經典時代‘禮法’這類字樣恰也常常是這四者的渾稱。”
這位譯界名師,精準把握了中國古代法的實質,複活了荀子的“禮法”範疇。
這裡所謂之“禮法”,并非将“禮”“法”視為兩個實體的“禮 + 法”“禮與法”“禮率法”,也非“引禮入法”“禮法合一”“禮法結合”之“禮”之“法”。它是一個雙音節漢語詞彙,一個法律概念,一個法哲學範疇。中國古代法,實為“禮法”法,“律令法”隻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法及以之為主體的中華法系,是一個“禮法體制”,或曰“禮法法系”。“律令體制”是其中一個子體制、子系統,還有“禮典”“禮俗習慣法”兩個子體制、子系統。“三代”之“禮─刑”結構為中華“禮法體制”的原始形态,漢以後重建的“禮─律─禮俗”結構為新型的“禮法體制”。
古代中國,欲長治久安者,所尚非“刑”,非“刑治”,非法家之治,而是尚“禮”、尚“禮法”,崇尚據“禮法”的“禮法之治”。唯“禮法之治”,而成就“禮義之邦”。
八.結語
前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家類”按語中還有幾句要緊的話:
“刑名之學,起于周季,其術為聖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于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于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
“四庫全書館”以紀昀為首的這些儒學館臣們,對管、商、韓這些原始法家及其著作的評價是否定性的,不是說他們“近功小利之隘”,就是冠之以“刻薄寡恩之非”,并一言以蔽之曰:“其術為聖世所不取。”其實,這也是秦漢以來一千多年的主流思想和價值取向。
論者或曰,曆代統治者搞的都是“外儒内法”,徒以儒家“仁義”裝飾門面而已。從宏觀高度對帝制統治術進行宏大叙事,可以這樣說。然曆朝曆代居然沒有人敢公開宣稱施行“專任刑法”的法家之治,不敢高舉一面“外法内法”旗幟,而需要儒家“仁義”加以修飾,這本身就已說明其緻治的治道之所在。說到底,這是獲取政治統治合法性的需要,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況且,法家之“法”之“刑”的有關元素,已融入“禮法”,連“法家”這一學派詞義,也已消融在 2.0版、3.0 版的新儒學之中。如前文所述,在具體案件的定谳上,儒家也主張以律定罪、嚴格執法,與法家之“一斷于法”同調。如宋代大儒朱熹就對惑于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而故出人罪的典獄官吏大張撻伐: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
“外儒内法”之論,或是對帝制統治者殘忍本性的一種揭示,然而,恰也說出了他們不得不施行“禮法之治”的那種不情願和無奈。畢竟,祖宗在馬上打下來的江山還是得下馬來治理的。
細究起來,将古代帝王統治術歸結為“外儒内法”之類的說法也是不确切的。如上考論,兩漢後所稱“法家”,已非先秦那個法家學派和法家治國之術,其嚴格執法、依律治罪的刑事司法主張已被吸納融合于經過改鑄的儒學之中。像朱熹、王陽明之類大儒主政一方時,在刑事政策上既講慎刑、恤刑,又嚴于治罪,殺伐決斷毫不猶疑。儒法已為一體,外是儒内也是儒。“輕罪重刑”“嚴刑峻罰”是商、韓的主張,但“法”不是先秦法家的知識專利。“禮法之治”中原本包含民本的教養之道和懲兇罰罪的刑事手段。胡蘿蔔加大棒,“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兩手齊備,兩手都硬,兩手都真。這便是秦漢以後的儒道。
絮叨那麼多,歸結起來很簡單:
無論是“尊主卑臣”、君主“獨斷”“獨制”的法家之治,還是“專任刑法”“重刑輕罪”的法家之治,都與我們追求的法治風馬牛不相及;帝制中國時代的統治者欲長治久安也不得不倡行“禮法之治”,而不敢效仿秦代法家之治。
現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