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發表于《湖湘法學評論》2023年第2期(總第8期)“學術專欄”欄目
【作者】史一舒,法學博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3网站太阳集团講師
【摘要】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是我國環境司法的新事物,在司法理念和實踐上,要特别重視并處理好能動性與謙抑性的辯證關系。環境司法能動性因應“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雙重困境,而環境司法謙抑性則是環境司法權适度擴張後,尊重環境行政權積極行使、恪守司法權行使的原則與底線。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特殊的防禦屬性意味着當行政機關“風險預防不能”時,法院需要積極主動地實施預防性、填補性程序措施。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司法能動性體現為“實體利益調整型”和“技術(程序)調整型”兩種模式。現階段,我國應以特色案例指導制度為代表的“實體謙抑”方式為基礎,并輔之以程序為取向的司法審查、預防性程序的适用等“程序能動”方式,以尋求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間的相對平衡與協調,并實現對環境保護中各種“左和右”錯誤傾向的司法校正。
【關鍵詞】環境司法;生态環境損害;能動性;謙抑性
一、瓶頸:生态環境利益擴展與調整機制失靈
2018年5 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目前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的攻堅期”,彰顯出國家基 于生态環境價值破壞提出的生态利益訴求已提高至對精神層面的更高需求。傳統法律框架内“公民 基本權利保障”“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私主體合法權益”,以及環境法發展早期的“無害” 或“害輕”已無法完全适應人們對持續提高生活品質的迫切需求。 環境司法是國家生态環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其在發展進程中突出強調的“綠色司法”“環境司法專門化”“鼓勵環 保組織依法開展環境公益訴訟”“法院與檢察機關、行政機關的聯動”等,均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當代環境法治的運行軌迹和進化趨勢,并使生态環境治理的運作模式呈現“多元主體互助、多種方式整合、多維訴訟并舉、保護弱者利益”的整體性态勢。這與生态價值充分實現和生态功能全面優化的“優美”生态環境相互呼應,更是當下中國社會發展部署中對公衆利益保障與普遍社會需求之間 關系的法律層面回應。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推進生态文明建設與 綠色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生态文明司法保障意見》)中提出公益訴訟案 件審理須以審判規律為基本前提,“适度強化能動司法,創新審理方法和裁判方式”,意味着我國環境司法将從“事後填補型”向“事前修複型”邁進。生态修複強調生态系統的完整性和穩定性,既要彌補已産生的損害,使生态系統在科學技術範圍内“恢複原狀”,又要對有損害可能的行為進行事先預防和保護, 維持自然生态系統的永續存在和可持續利用。我國環境司法的發展路徑呈現“民事損害救濟—環境損害賠償—環境公益訴訟—生态損害賠償”的利益擴張與綜合發展趨勢,客觀上要求司法理念和方式要積極适應生态文明建設的需要。
截至2019年6月31日,近五年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環境資源一審案件108 萬餘件,審結103萬餘件,全國共有環境資源專門性審判機構1201個,其中環境資源審判庭352個,合議庭779個, 巡回法庭 70 個,其中15 個高級人民法院實行“二合一”或“三合一”歸口審理模式。并且,部分法院通過創新适用“補種複綠”“增殖放流”“勞務代償”等新型責任承擔方式,确保生态環 境的及時全面修複完善,依法維護人民群衆在健康、舒适、優美生态環境中生存發展的權利。随着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幹規定(試行)》(以下簡稱《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發布,我國法院創新賠償協議司法确認程序、發布環境訴訟禁令、加大專家有效參與審判的力度, 注重生态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公益訴訟程序的有序對接, 将“綠色司法” 中生态修複型司法理念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時環境司法已不單單具有消極、被動的屬性,而更具備積極、主動的行為模式。但與此同時, 與司法能動對應的司法謙抑問題開始受到進一步的關注。一方面, 司法謙抑是樹立司法權威的必要保證, 司法“有所不為方能有所作為”;另一方面, 當代“行政國家”運作中産生的“官僚主義泛濫”和“極權主義行政行為”無法處理不确定環境風險帶來的多維度生态難題,法院的創造性司法過程為生态價值的重新确認提供可能。在司法謙抑與司法能動協調境遇中,由于社會發展水平與法治發展階段的約束,我國現階段環境司法能動是有限、有邊界、有條件的能動,同時環境司法需要能動并不意味着司法能動可代替司法謙抑。司法謙抑性是司法能動性的前提和基本條件,是環境司法運行應當恪守的準則和底線。如果司法不顧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定,忽視普遍正義與特殊正義的平衡,在任何情形下都一味追求能動,其結果隻會颠覆司法的本性,使司法完全淪為利益工具。能動性與謙抑性均為環境司法所必需,環境司法能動的界限是本文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環境司法能動性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雙重背景下尤為突顯,一定程度上是對此二種失靈的司法補救。“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但在環境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近年來尤其表現為生态環境保護政策法律實施忽左忽右,既有消極被動不作為,也有不當能動亂作為。例如,一個數千元的污染損害賠償訴訟請求,損害鑒定的費用竟高達數十萬元,使司法陷入困境。一方面“企業污染、公衆受害、政府買單”有蔓延之勢,這是環境保護中“右”的傾向;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綠左”盛行, 環境執法“一刀切”,為追求環保政績搞“無豬縣”“無雞村”,環保産業“綠色大躍進”,打着綠色旗号圈地圈錢。究其原因,其一,“市場失靈”是環境問題長期存在的首要原因,環境問題具有高度科技關聯性與系統性的特點。在時間維度上,環境侵害具有長期性、潛伏性和不可逆性,“任何被忽略的不确定的科技風險都可能對環境造成緻命打擊”;在空間維度上,環境侵害涉及跨區域和跨介質層面,并關涉污染物質相互遷移、影響與轉化問題,因此環境問題在本質上是難以孤立、不可分割的。而“負外部性”是經濟分析中環境污染和生态破壞的重要成因,加之生态環境具有非排他性、無償性的公共品屬性,導緻公共品遭到濫用的“公地悲劇”及無償享有公共品利益的“搭便車”現象。當前我國試圖在生态修複市場化“企企合作”中加強企業市場地位,将“誰污染、誰治理”轉向“誰污染、誰付費、第三方修複”。不過,由于市場監督管理不暢與責任界定不清、相關行業專業化程度較低,生态修複遠未達到預期效果。經濟學家庇古曾提出,通過對負外部性行為征稅或收費等“命令—控制”型政府适當幹預的行政管理方式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弊端。其二,以環境規制為主的傳統環境管理機制已難以解決生态環境保護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困局,形成企業污染、公衆受害、政府買單的環境非正義格局。生态環境損害具有複合性及損害價值的難以估算性,傳統秩序行政所主張的“經驗法則”已無法應對瞬息變幻的潛在環境風險,損害擔責、排污收費、排污許可等強制型環境法律原則和制度頻出應用失衡和規制失衡的問題,立在行政機關面前的是一塊“未知之幕”,如果不采取規範措施則有可能導緻不可逆危害的發生。因此,“決策于未知之中”的環境風險規制應運而生。風險規制實質是官僚與專家系統代替人民決定是否接受特定風險的過程,是“指向未來的法律決定”或“法律對于時間的一種處理”,涉及風險評價、信息公開、風險權衡、決策補救方式、利害關系人和公衆參與等諸多内容,任何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緻不可逆危害的發生,我國近年出現的如福建省廈門市、廣東省茂名市等地 PX 項目群體性事件,即是由政府風險規制判斷與公衆風險認知間的巨大反差導緻的。此時,将私人或公權力機關訴訟作為實施工具的環境司法成為風險環境規制“缺失”的有益補充,通過積極主動制約潛在違法行為,及時降低行政機關被“俘獲”的風險,有效監督并督促行政機關積極執法,以彌補公共執法資源的不足。積極能動的環境司法與環境行政的“合作規制”聯動路徑即具有一定空間與可能,是克服“兩個失靈”的有效保證。
二、比較與趨勢:我國環境司法能動之定位
(一)司法能動之溯源
我國司法能動起源于西方的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其在西方有兩個理論來源,即美國的“憲法司法化”和歐洲的“對傳統概念法學的反思”。二者均強調“司法中心性”, 奉行“通過廣泛司法推動社會各方面進步”的司法觀,法官不應僅依靠先例或成文法導出裁判結果,而應密切關注現實社會發展需要,創造性地通過解釋補充法律,并合理運用權力促進公平并保護人的尊嚴。其中美國是以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為根基、以“司法審查”為起點而廣泛實施的司法能動主義。在 1803 年“馬伯裡訴麥迪遜”一案中,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首次提出“司法審查是一種獨特的憲法解釋”,法院具有解釋憲法的最高權威和最終效力,并确立“法院有權宣布一切與憲法違背的法律無效”原則。歐洲則将“法官造法”理念指導下的審判活動演變為一種實用藝術,法官判決是彌補判例法存在滞後性的必然選擇和法律實現的重要途徑。德國著名學者漢斯 • 普維庭教授指出,法官造法在所有法秩序中都是必要的,其核心在于造法的界限問題,比如法官須通過程序法限制并制約造法行為。我國“能動司法”與司法能動主義具有某些相似性,根本目的都是在司法權的行使限度内使社會福祉最大化,但在内涵、适用主體、适用方式等方面,兩者存在根本區别:(1)在内涵上,司法能動主義是“通過司法否決或改變法律”,能動司法則強調“在司法權的限度内,法院通過主動發揮個人或集體能動作用,積極解決社會糾紛和案件”;(2)在适用主體上,司法能動主義是以個體價值和意義為中心,體現的是每個法官對司法裁判理念和方式的選擇,能動司法則是法院和法官具有統一性、整體性的司法理念和裁判活動;(3)在适用方式上,司法能動主義鼓勵法官在特殊案件中超越先例、推進公共政策生成的“造法”,能動司法卻以法律統一适用和統一實施為基礎進行司法解釋和裁判案例指導。我國能動司法曆經“職權主義限縮—當事人主義擴張”訴訟模式變化過程,最早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王勝俊于2009年提出的,具有服務型司法、主動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三個顯著特征。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實施前,司法權在相當程度上壓制并限縮當事人的基礎訴權,各級人民法院遵循“法官擁有廣泛訴訟管理權、指揮權和主導權”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如法官具有庭前實體審查權和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權,并且不受“辯論原則”的嚴格限制。随着《民事訴訟法》的頒行及審判模式改革的不斷推進,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逐漸取代“當事人說破嘴,法院跑斷腿”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官對訴訟過程的職權幹預被削弱,當事人訴訟地位得以加強。但作為法律移植型的法治建設國家,我國三十餘年來長期秉持“立法中心主義為綱”的思維模式,延伸至司法審判中則出現“重視法條主義的司法審判過程,輕視具體的權利救濟和糾紛解決”現象,“完全當事人主義”難以克服司法裁判中實體及程序正義缺失的弊病。由此,能動司法對于适當強化職權主義、鼓勵法官進行法律漏洞填補、推動實體和程序規則變更發揮了積極作用,使法院和當事人在一種充分對話和溝通的審判程序中實現裁判公正。
(二)環境司法能動性之表征
當前,環境司法能動是對我國環境法律規則的适當拓展與突破。盡管我國已初步形成與生态文明和綠色發展相适應的生态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但由于立法的局限性,立法質量與精細化程度不足,原則性規定較多、法律規定存在重複或沖突、操作性較差,現行環境法律制度難以适應快速轉型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此,司法能動是現階段環境治理多元主體有效互動、多重利益合理分配目标下的必然選擇。當前域内外環境司法能動性具有如下三個表征:
1.環境司法能動形式的多元化
國外環境司法較其他司法領域在能動性上的表現更具積極性和廣泛性。布拉德利 • 坎農曾提出法官“運用實質推理、使用實質價值性修辭、通過判決之外的補充意見”等 17 個參數描述司法能動主義的具體形式。各國環境司法能動呈現出多種表現形式和複雜維度:(1)在公共政策形成與立法方面,日本通過司法控制政治繼而改變法律使公共利益得到長久的根本性維護。(2)環境案件管轄打破地區分割式傳統方式,而代之以水、空氣等環境要素自然屬性與生态系統特性的跨區域管轄。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典、日本、南非、孟加拉國、印度、科威特、肯尼亞等國家均已通過成立環保法院或設立環保法庭的方式實現環境審判靈活與效率的統一,美國“佛蒙特州環境法院”設置特殊程序規則(《佛蒙特環境法院程序規則》)實現環境案件的專門化、專業化審判。(3)在環境司法審判程序與庭審風格方面,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先行調解程序的應用、專家輔助人的有效參與等能動實施方式較為廣泛,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土地與環境法院是由來自上訴、民事及刑事工作三個主要司法管轄區的非專業專家及法官組成的特别法院,新西蘭《資源管理法》(New Zealand’s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of 1991)規定環境法院的組成包括具有與環境争端相關領域專業知識(如商業、經濟和地方政府事務、規劃和資源管理、環境科學、建築和工程等)的環境專員。較之域外各國,我國環境司法能動主要體現為規則治理中的理性創新,包括法律規則的漏洞補缺和實體及程序規則的适當突破,強調法官在調查取證、訴前禁令、專家參與、舉證責任分配、判決執行等方面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個案特征”較為明顯(表 1)。如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訴北京多彩聯藝國際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大氣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案”中,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不僅創新環境訴訟實體規則,明确“虛拟治理成本法”在大氣污染損害評估中具體适用方式,并多次采取預防性程序措施,包括案件受理後的“行為保全措施”和案件審理中“禁止生産的預防性裁定”。在“貴陽市生态環境局訴貴州省六盤水雙元鋁業有限責任公司、阮正華、田錦芳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中,法院不僅在調解書中列明“被污染地塊修複的負責單位、具體修複方式、修複啟動時限”,而且對判決生效後法院的具體監管職責、監管時效、監管範圍加以明确。在“中華環保聯合會、貴陽公衆環境教育中心與貴陽市烏當區定扒造紙廠水污染責任糾紛案”中,清鎮市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前采取拍照、取樣等證據保全措施,與環保部門協調聯動,即時采取措施制止被告及其他紙廠的排污行為,最大限度保障生态修複目标的實現。

2.司法審查在環境司法中呈擴張之勢
司法審查在不同國家法律制度環境中具有不同含義。一般來說,司法審查是由國家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法規、規章,以及行政機關相關行政行為的合憲性與合法性作出認定。在傳統秩序行政下,行政規制合法性基礎被概括為“傳送帶”模式,即行政權來源于民意機構的立法授權且其行使須遵循正當程序,并受到司法審查的制約。而随着風險社會的來臨,環境風險規制已然由政府主導的單向行政命令模式轉化為市場、公衆“多元參與、協商民主”規制治理。相應地,司法審查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防止行政機關對私人自治領域未經授權的侵入,而是确保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公共)利益在行政機關行使法定職權的過程中被公平地代表,實現此目标的重要方式即拓寬公民的起訴資格與司法審查的程序範圍。通常情況下,行政訴訟是司法機關實施司法審查、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認定的重要途徑,如德國環境案件司法救濟主要通過行政訴訟。2002 年,德國《聯邦自然保護法》賦予環境團體享有廣泛的訴權,可對即将或正在實施的“政府有關自然保護區、國立公園的保護或解除禁止事項的命令”及“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可能有損環境的行政許可或政策”提起訴訟。而在日本,針對火力發電站、高速公路等公害事件則采取“事前中止訴訟”的形式。
美國被稱為司法審查制度的母國。19 世紀至 20 世紀,美國司法審查範圍呈現大幅擴張态勢,除法律明令禁止和行政機關正當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外,一切行政行為都須接受司法審查。在1984 年“謝弗林訴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案”(Chevron v. NRDC)後,最高法院不斷超越審查邊界、抑制環保署裁量權行使靈活性并持續修正謝弗林規則,提出就事論事的“司法最低限度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以便為此後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留有較大空間。盡管我國《行政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 53 條僅允許對“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範性文件”在提起行政訴訟時進行附帶性審查,但環境司法審查“觸角”卻遠超上述範疇,具體行政行為及與司法機關行使審查權相關活動均可被稱為“司法審查”。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江必新曾強調“注重對環境資源行政規制的司法審查,依法做好權限審查、事實審查、法律适用審查、程序審查和濫用職權審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26 條對公益訴訟撤訴程序作出規定,其中基于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告處分權的限制而賦予法院司法審查權,法院應通過主動的職權幹預形式對原告“訴訟請求全部實現”進行合法性審查,以作出是否準予撤訴的決定。
3.檢察機關對環境司法能動之強化
與審判機關積極主動的步調相一緻,檢察機關在環境司法中亦承擔着遠超“追究刑事責任、提起公訴和實施法律監督”的職責範圍。自 20 世紀 60 年代後,為遏制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檢察機關職能擴張、獨立性加強,并被賦予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曆史使命。巴西《公益訴訟法規定》中明确“檢察機關有權在環境民事調查中實施‘庭外調解前置程序’并得以‘行為調整協議’結案”。俄羅斯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完全分離,是具有專門監督職能的“護法機關”,聯邦檢察院檢察長有權要求環境行政機關履行一定行為,如進行環境污染和破壞情況的檢查、選派專門人員向法院和仲裁法院提起訴訟、向檢察院提供環境案件相關的重要材料和證據等。美國檢察機關具有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衆利益的案件直接通過民事或行政訴訟方式進行法律規制的廣泛權力,《國家環境政策法》《清潔空氣法》均賦予檢察機關單獨提起公民訴訟權,“私人檢察總長”(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理論即以此為基礎賦予美國公民個人或組織通過私人訴訟的方式保障公私利益的權利。
從世界範圍内看,檢察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是我國的獨創制度。2015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方案》,随後我國《行政訴訟法》(2017 年修正)第25 條、2018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 21 條均規定檢察院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制度,主要包括“訴前檢察建議程序”和“針對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職的訴訟程序”兩個部分。訴前檢察建議是針對妨礙檢察目的之實現的違法或不當行為,通過具有相對靈活性的書面形式向特定被建議對象提出糾正、處理或改進意見的非強制性檢察程序。訴前檢察建議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前置程序,實質是通過司法審查督促環境行政執法内部救濟與自我審查的實現,具有強化訴前協商程序、節約訴訟資源的直接效用。2018 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類案件 59312 件,其中辦理訴前程序的案件有 53521 件,經訴前程序行政機關整改率達 97%,在“湖北省黃石市磁湖風景區生态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中,檢察機關通過訴前檢察建議的方式,有效解決因多個行政機關職能交叉、權限不清而産生的執法難題。
由此,檢察機關環保督促履行職責不僅是對行政權的“一般監督”、對公安、監獄等部門“司法監督”或“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而且是更具公共意義的,兼具主動性、積極性、能動性的法律監督方式。
三、特殊公益訴訟司法謙抑性之不可或缺
(一)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本質是特殊的公益訴訟
我國正在試行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賦予審判機關較大的司法裁量權,這對正确理解和發揮環境司法能動提出更高要求,司法謙抑性理所當然地進入人們關注的視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謙抑必要性與制度特色的識别首先需要明确其所救濟的利益類型。“生态環境損害”指的是對(生态)環境本身造成損害的法律事實。美國法中用“自然資源損害”(natural resource damage)表達與“生态環境損害”相同的含義。原環境保護部 2014 年發布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4.5 條與 2017 年國務院發布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将“環境和生物要素的不利改變”“生态系統功能退化”和“生态系統服務能力的破壞或損傷”作為生态環境損害的識别要素。生态環境損害賠償不同于“生态補償”,前者是由違法行為導緻的“負外部行為”,而生态補償是對合法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的物質補償,是指為平衡公衆生态利益,由生态受益者(中央或地方人民政府)向合法利益受損的組織或個人,以财政轉移支付等多種形式進行補償的法律制度。由此,生态環境損害專指由具有可追責性的環境污染和生态破壞行為引起,與人身損害、财産損害并列的生态環境本身的損害,損害後果可能是以環境為介質,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财産、精神損害,抑或是隻有對環境本身的損害,而沒有可歸屬于具體個人的損害。對此,“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第 2 條明确訴訟救濟範圍,排除“個人人身損害、集體财産損失”等私益救濟可能,僅立足于對生态功能價值等生态環境本身的公益救濟,這與環境公益訴訟的救濟範圍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性。
根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18—20 條與《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 11 條規定,此二類訴訟的訴訟請求通常要求責任人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預防性》民事責任及生态修複、直接支付賠償費用等“事後填補型”民事責任,同時《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2條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侵權責任糾紛司法解釋》)的參照适用規則予以明确,因此有學者認為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是一類《特殊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或其實質即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本文亦認同此觀點。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是政府基于“自然資源國家所有與公共信托環境權益”的二維權利基礎構造,對環境公共利益進行維護的特殊民事訴訟形式。不過也應注意到,二類訴訟起訴主體差異性決定了訴訟模式構造的不同利益傾向(表 2)。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告是符合條件的“對舉證存在障礙”的法定社會組織,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起訴主體是公共物品的主要供應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具有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強勢行政機關,加之其在環境規制活動中豐富的環境案件技術性檢驗、監測、評估證據材料獲取途徑,同造成生态環境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相比占據了訴訟地位和訴訟能力的相對優勢,由此原被告雙方的極度不平衡關系被打破。可以說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起到了對“手段匮乏”的環境監管與環境執法活動的補強作用,它的重要功能即是通過行政機關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遞進式履行”與“自我反省”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實現。
以此為基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的關系銜接應秉承“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為先——環境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為補充”的順位安排,這在“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中體現為第 16 至 18 條的規定。換言之,針對同一環境污染或生态破壞行為,生态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在同一時間段内被提起,行政機關提起的生态環境損害訴訟具有“先行審理”或“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合并審理”的資格;當“行政機關所主張之訴求不足以修複與賠償受損生态環境”或“有證據證明存在前案審理時未發現的損害”時,符合法定條件的環保組織或檢察機關才可作為後備力量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如在“山東章丘‘10 • 21’重大非法傾倒危險廢物案”中,由于涉及刑事案件的審理,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作出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止審理”裁定後,對山東省環保廳所提起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件進行“先行審理”;而在“江蘇德司達公司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和“重慶藏金閣公司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中,法院基于訴訟标的一緻性及節省司法資源等方面的考慮,對先後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作出“合并審理”的決定。根據我國《憲法》(2018 年修訂)第 26 條、第 89 條之規定,國務院負有“領導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設”之職責,環保行政機關亦負有“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之職權,二類訴訟的訴訟順位安排應符合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危險防禦義務”之司法展開,即國家應順應環境基本國策中對公權力的“以預防并排除環境危險為中心”的要求,将行政活動“追求公益”的行為目的适當擴張至司法領域。其中,在“根本性損害”發生前,檢察機關督促行政機關履行相應“預防性職責”,發揮了關鍵作用:經檢察機關發出訴前檢察建議後,行政機關積極履行法定職責、進行磋商或提起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啟動程序終止;倘若行政機關仍怠于履行環保職責,經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後才進行磋商或提起訴訟使檢察機關訴訟請求實現的,行政公益訴訟程序中止,待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審結後,檢察院可變更訴訟請求。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縣人民檢察院訴清流縣環保局行政公益訴訟案”中,在訴訟期間清流縣環保局對劉某非法處置廢物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而後清流縣人民檢察院将訴訟請求變更為“确認被告清流縣環保局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違法”,因此行政機關的糾正違法、提起訴訟行為可不完全阻礙監督檢察權的行使,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作為對行政機關的補充性懲罰程序得以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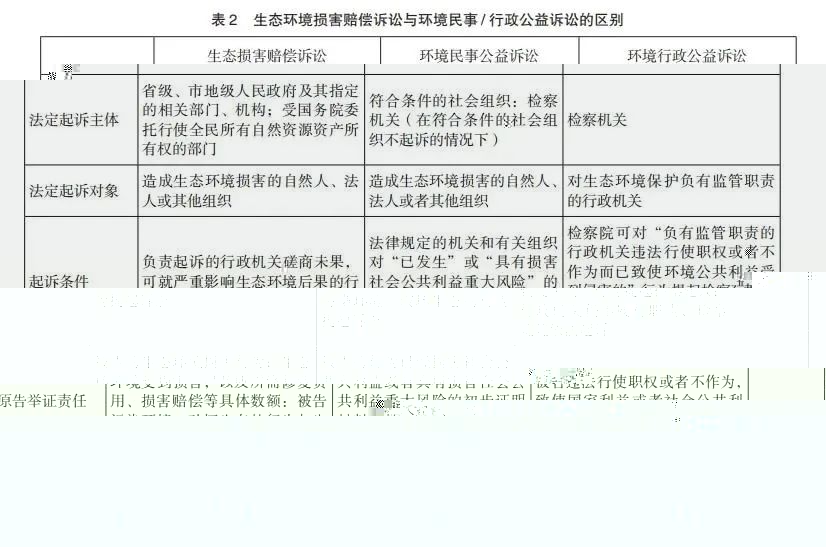
(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謙抑性之呈現與适用
司法謙抑是與司法能動相對的概念。司法權是消極被動的權力,因而具有謙抑性。在功能性謙抑中,它要求審判權的啟動必須恪守不告不理等基本原則;在結構性謙抑中,司法權不得逾越立法權和行政權行使的法定範圍和限度,反對司法權過度擴張。司法謙抑作為司法的固有邏輯,是防止自由裁量過度行使、維護司法權威性的重要法律理念,要求在技術理性的前提下,嚴格遵守法律的形式正義。法官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權,并須加重“超越法條司法”的法律論證負擔和“判決依據及考量”的具體闡明責任。“司法謙抑主義”源于 19 世紀後半期,社會經濟安定對“法律安定性”寄予期許,英國主張把法官裁判視為法律形式論理演繹與概念的機械組合。一方面,司法謙抑秉承德國法教義學“法條主義”路線。按照阿列克西的經典概括,法教義學的基本工作涵蓋概念分析、概括整合,并将整合結果适用于司法裁判三個層次。另一方面,司法謙抑體現的是裁判說理層面“最低限度法治”的要求,将價值目标上法的安定性與制度目标上統一融合的法律體系作為基本要素。我國司法謙抑是技術性司法背景下形式法治主義的彰顯,比如在道德權利“法律化”過程中,司法應抑制道德權利的泛化;刑事司法基本屬性“消極性、被動性、居中裁判、注重傾聽”與謙抑原則主張的“最少幹涉、保障基本人權”高度契合;在民事審判中,審判權能的限定性、解紛範圍的有限性、程序啟動的被動性、程序控制的相對性、裁判效力的安定性是司法權克制與寬容的重要外在表現形式。具體到個案司法審判中,司法謙抑要求法官應充分尊重規則的權威,反對超越法律規則框架的“法官造法”和“例外性司法”;即使在疑難案件中,法官仍需遵循法律而非個人的道德判斷和國家的政策傾向。
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謙抑性是環境行政權适度擴張至司法領域後,環境司法恪守司法權行使原則與底線、尊重行政權積極行使的體現。一方面,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隻有在窮盡行政救濟後才得以啟動。各級政府應用盡所有可操縱資源實現填補環境資源損失、恢複生态環境功能等行政機關在生态文明建設上所擔負的特殊憲法責任;倘若仍無法實現,政府提起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方具有合理性。概言之,“立法确立公益,行政執行公益,司法守護公益”。不同于西方三權分立體制,我國是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全國人大權力賦予下的不同職能分工,行政權的本質是管理權,而司法權的本質是判斷權。行政機關通過提高行政活動的效率,協調并不斷改善行政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以維護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而司法監督行政,司法審判是權利救濟的最後一道防線。雖然司法權與行政權在法律明确規定情況下可“相互替代”,但在環境公共事務管理問題中,行政權往往具有優先效力,當前政府由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履行者異化為環境問題的制造者和加劇者,規範并督促政府對環境公共利益的積極維護應成為環境保護的主要方式。在确保污染者成本内部化的同時,行政機關在“損害補救方案的制定、決定與執行,補救工程驗收”等損害治理方面具有專業性和高效性。當行政機關在其權限内無法徹底解決問題、錯誤或怠于履行其法定職責時,司法機關才可作為行政執法監督的補充或延續,通過私益或公益訴訟的程序介入,從而達到規範權力配置、節約司法資源的法治效果。尤其在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行政裁量權行使中,法院應對行政機關法律框架内行為給以相對自由的發揮空間。由于公共行政活動的複雜性、不确定性,行政機關被賦予特定情形下對如何“作為”或“不作為”進行選擇的裁量權力。“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第 1 條中規定“磋商前置”程序設置及“嚴重影響生态環境後果”法定适用情形意味着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必須首先經過一系列行政執法程序,當行政命令、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手段中的“責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修複環境”等矯正違法和填補損害措施無法适用于嚴重生态損害的情形時,生态損害賠償才能步入司法軌道,明确了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權力運行順位。事實上,行政磋商在 2015 年《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并非行政機關提起索賠訴訟的必經程序,但此後《改革方案》《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及北京、河南、山東、江西、河北、浙江等地制定省級生态損害賠償實施方案均遵循“規制行政優先——索賠訴訟兜底”制度設計,體現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對協商性行政執法的後續補強功能。
另一方面,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程序運作過程中法院應對行政機關法定職權的行使予以最低限度的保障。據前所述,當案件未達成賠償協議或因客觀原因行政機關無法與被告進行磋商時,行政機關将作為“特殊民事公益訴訟”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原告提起訴訟,視為“環境公共利益的直接捍衛者”履行環境監管權手段之延續。“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第 9 條“行政執法證據運用規則”、第 10 條“環境司法鑒定證據運用規則”等均顯現出環境行政與環境司法證據銜接的互通性與連貫性,行政機關在證據收集方面覆蓋面廣、成本低、效率高,專業人員及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相較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雙方的訴訟能力與訴訟地位已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态,因而在《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第 22 條“參照适用”中,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諸多限制被告權利的條款應不再适用。自 2012 年公益訴訟被納入《民事訴訟法》以後,我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設計基本沿襲傳統環境侵權訴訟中“原告弱勢、被告強勢”的法律預設,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及《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更在環境侵權訴訟的原有規定中限縮被告訴訟權利,使得作為拟制主體的原告幾乎突破所有依據“正當當事人理論”帶來的程序制約而進入一種不受約束的訴訟狀态。比如《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8 條繼續适用環境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即原告僅具有損害結果及損害與污染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的初步證明責任,而被告如無法否定因果關系之存在,即可推定因果關系存在;第 16 條“否定原告自認規則”、第 17 條“限制被告反訴規則”等均違背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則,剝奪被告方在訴訟中自由處分權利的可能性并加大其防禦難度,此類條款應不再适用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此外由于行政機關在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獲取證據的自由度、便捷度、廣泛度較強,法院的能動作用也将部分轉化,比如《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14 條“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權”的參照适用應予以适度限制。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法官不宜再通過職權幹預來平衡雙方訴訟能力、舉證責任分配等實體利益關系,而應以謹慎、謙抑、中立的态度,注重審查“訴前磋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被告是否獲得了應有的程序性權利”“案件可否适用調解”等基本訴訟程序設置,充分尊重行政機關實體性職權之行使。
四、程序理性之風險: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
司法能動的結構性瓶頸
(一)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能動之呈現與适用
環境司法是一個追求正義的能動性與結果導向的利益平衡性并存與博弈的過程。博弈是在遵循既有規則的前提下追求一定利益最大化,博弈效果則取決于博弈主體的正确決策和行為優化,其中每個主體的決策、行為都可能相互影響乃至相互沖突。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謙抑性關乎司法權行使的限度,而生态損害賠償責任特殊的防禦屬性意味着法院無法時刻保持克制謙抑的姿态,當行政機關“風險預防不能”時,法院需要積極主動地實施預防性、填補性措施,此時需要在司法謙抑與能動的博弈中尋求利益、衡量正義。環境保護是行政機關針對風險而面向未來作出的危險防禦活動。長期以來,我國環保法的立法與實施方式均由行政機關主導。由于立法者專業環境科學知識的缺乏,其隻能通過法律委托行政機關的方式,制定生态環境保護法規及環境質量标準體系等行政管制标準;而實施中行政機關的執行性和主動性在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履行中實現較大延展,并不斷将預防性理念貫穿至環境行政行為或行政救濟的全過程,通過對行政相對人排污或其他有生态破壞可能的行為進行監測與監控,對産生嚴重影響生态環境後果的行為人課以行政命令、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法律責任,以求達環境規制法律體系的統一運作。應當看到,雖然生态環境部與自然資源部的組建有利于解決我國過往環境保護體制長期存在的權責不明、多頭執法、效率低下等問題,但關乎環保執法績效的細節性問題遠未解決,如行政違法責任遠不足以抵消環境違法的收益、财産罰額度過低、行為罰适用極少等,以緻出現“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行政處罰執行難”“重行為模式、輕法律後果”等現象,難以實現對“生态環境本身損害”的充分填補與有效救濟。為保障環保命令的有效執行和增加企業違法成本,2014 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增加“按日連續記罰”制度,但由于其法律性質不明、計罰标準單一,其在實踐中使用率極低、适用的違法行為類别較少。
為應對環境風險的不确定性及政府行政監管的缺失,生态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能動過程體現出明顯的前瞻性,此前瞻性不同于“司法超前”,而是針對環境質量下降或生态破壞狀況事前采取預測、分析和防範的司法措施,包括預防性司法救濟與責任方式的建構等。基于盧曼和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風險具有主觀和客觀的雙重面向,而風險預防的程度是綜合價值判斷的結果。根據《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 1 條的規定,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範圍相對較窄,僅涵蓋“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發環境事件”和“國家和省級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劃定的重點生态功能區、禁止開發區”内發生的“嚴重”生态環境影響類案件,前瞻性生态損害賠償訴訟能夠在難以修複或危害範圍較廣的嚴重損害結果既定前,積極對環境損害行為或存在環境損害之虞的行為進行事前阻卻,調節并平衡包括環境公共利益在内的各方利益關系,因此預防性措施應是生态損害賠償訴訟的目标。
其中預防性責任承擔方式呈現出多樣性與私法性,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保全及禁止令等多種民事責任形式。《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第 11 條直接“借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合理判定污染者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生态損害加劇或環境污染嚴重擴散前的預防性民事責任承擔方式的規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9 條“法院釋明權”的參照适用亦體現了法院的判決既定前的事前防禦與不利結果化解功能。在江蘇省第一起由省政府單獨提起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江蘇省人民政府訴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原審法院釋明并無不當”,并根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9 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 232 條的規定,認可“當原告訴訟請求偏少而不足以保護公共利益時,法院釋明變更訴訟請求”的合理性。此外,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法院的預防義務還包括行為與證據保全等,根據《環境侵權責任糾紛司法解釋》第12 條規定,環境民事私益訴訟與公益訴訟中的預防措施主要為保全措施,《改革方案》中規定“各地人民法院要研究符合生态環境損害賠償需要的訴前證據保全、先予執行、執行監督等制度”,其中上海、浙江、河北等地均發布相關規則,如上海市在《關于審理政府提起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民事案件的若幹意見(試行)》中補充規定“在證據保全過程中,可以邀請相關專業部門、相應領域的技術專家等共同參與”。
域外環境司法能動性與謙抑性的博弈重點體現在氣候變化領域。近些年以美國、澳大利亞為代表的氣候變化訴訟數量大幅增加。盡管美國政府與科學專家、公衆間因缺乏有效的風險溝通程序而争議不斷,并且美國環境署屢屢依據各種理由拒絕規制溫室氣體排放,不過國内各方已通過司法程序展開氣候變化問題的利益博弈,法院已成為有關氣候變化的法律、政治和社會交鋒的“戰場”。截至 2014 年 2 月,美國氣候變化訴訟已達 635 件,主要包括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兩種類型,通常情況下屬于普通法侵權行為的類别——在起訴工業污染源的基礎上,主張過失、妨害或環境監管行為,認為政府決策制定并未充分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但侵權索賠訴訟仍面臨确立立場、證明因果關系、在多個貢獻源之間分攤責任等多個障礙。由于美國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并遵循“國内法與國外法區别對待”的二元論原則,美國氣候變化訴訟形成了有别于國際環境法的獨特規則與審判模式。如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的第一個氣候變化案件“馬薩諸塞州訴環保署案”(Massachusetts v. EPA)中,法院認為“原告有權對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拒絕根據《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監管溫室氣體排放的規則制定請願書的決定提出疑問”,并首次在環保團體的請願下對美國聯邦政府的環境規制決定進行司法審查,最終法院認可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害已得到“充分認識”,責令 EPA 與美國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将兩者的有關規範相協調;在“生物多樣性中心訴國家公路交通與安全管理局案”(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v.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and Safety Administration)中,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基于“溫室氣體排放對氣候變化的累積影響”要求該機構重新考慮其輕型卡車的燃油效率标準。相較于氣候變化行政訴訟案件的樂觀态勢,真正獲得經濟賠償的民事訴訟案件寥寥無幾。在“加州訴通用汽車公司案”(California v. General Motor)中,加州政府以妨害公共利益為由向多家汽車制造商索賠。地方法院駁回了這一索賠要求并認為這是個不可受理的政治問題,“解決這一索賠要求需要作出一項政策決定,将侵犯各政治部門的商業和外交權力,并且在一個完善的法律框架下是不可用的”。類似的案件還有“康涅狄格州訴美國電力公司案”(Connecticut v.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mpany)等。
由此,美國氣候變化角力已從政治領域轉至司法抗争,法官需要積極主動地評估案件事實可信度、貫徹規制政策并監督行政權力的正當實施、組織并塑造氣候變化訴訟程序,以确保結果的公正與切實可行(表 3)。其中,法院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即“可訴性”(justiciability),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規定,可訴争議“必須明确具體,涉及具有不利法律利益的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它必須是一種真正的和實質性的争論,并承認其可通過一項具有結論性質的法令獲得具體救濟”。雖然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内可訴性原則具有多樣實施框架,但“原告須有起訴資格”和“不得違反權力分立”這兩個基本要求是相同的。在澳大利亞,更嚴格的成本規則旨在阻止氣候變化投機性訴訟,并在州管轄範圍内政府通過立法限制氣候變化侵權救濟,因而澳大利亞的氣候變化訴訟走上環境/行政法的道路。近期此類案件主要有新南威爾士州 Anvil Hill 案、維多利亞州 Hazelwood 案、昆士蘭州聯邦法院 Wildlife Whitsunday 案,其中對煤礦和燃煤發電站建設提案所涉及的溫室氣體排放環評程序提出疑問。相較而言,我國的氣候變化立法、行政行為及司法訴訟略顯單薄。對此,有學者提出通過“法院職權幹預邊界前移”的方式,對普通行政行為及行政不作為進行預防性審查,以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确定風險。

(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能動之方法模式考量
在環境司法專門化改革進程中,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作為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将政府環境保護使命發揮至最大化,并成為執行環保法律、督促企業節能減排、鼓勵公衆參與環保的重要制度形式。在環境治理向“多中心模式”轉型、環境利益分配向弱者傾斜的環境司法改革趨勢下,我國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司法能動體現出“實體利益調整型”和“技術(程序)調整型”兩種模式(表 4)。前者指法院的能動偏好對環境糾紛主體結構、利益分配和利益關系直接作出調整,由此決定個案或類案實體裁判;後者指以完善環境審判技術、訴訟程序本身及相關程序銜接等技術方面為首要條件,以确保環境法律體系結構完整、框架充實,實現環保法體系的全面順利運作。如“實體利益調整型”能動模式典型案例——1995 年“雞西市梨樹區人民政府訴雞西市化工局等環境污染賠償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據 1991 年《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的規定,在法律文本缺漏時,運用經驗推理的形式将原告主體資格作擴大解釋,最終作出“梨樹區人民政府有權作為原告提起民事訴訟”的複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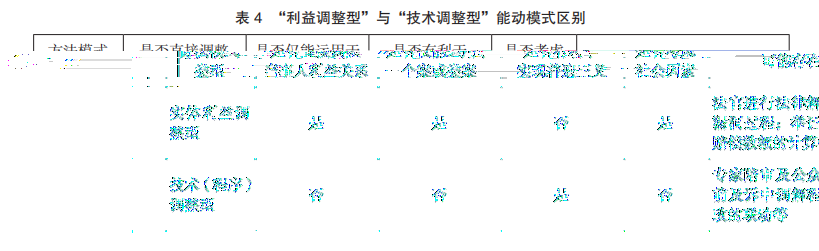
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存在利益沖突的必然性。随着社會從同質性利益結構向多樣性利益結構變遷,基于傳統視角下權力和身份為主宰的利益分配格局分化,逐漸形成不同利益群體和組織形式。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蘊含着“法院—政府—企業—公衆”與環境公共利益間事實與價值的錯綜複雜關系,僅依靠傳統“三段論”邏輯推理是遠遠不夠的。對此,有學者提出在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法官可以運用法律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内化外部性,以經濟方法分析改善資源配置類型和主體權力交易所需的代價和可能得到的利益,通過降低社會及司法活動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對生态環境資源利用不合理的開發利用行為造成的損害進行責任分配。美國對環境問題的處理常使用環境成本效益分析(Environmental Cost-benefit Analysis,CBA)方法,通過對政策和項目進行經濟評估以改善所提供的環境服務,或對不利環境影響項目采取行動。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發布以成本效益測量和可替代方案審查為重要内容的多部環保行政法規,包括《燃煤、燃油發電機組有毒大氣物質排放标準》(2011 年)在内的以改善大氣質量為基本目标或首要目标的法規所産生的收益占 EPA 十年間出台法規總收益的 98% ~ 99%,EPA 大氣辦公室發布的 27 項法規(獨立發布 24 項,聯合交通部發布 3 項),十年間帶來的效益為 1950 億~ 8996 億美元,成本為 464 億~ 620 億美元,效益成本比大于 4 ∶ 1。相應地,美國法院對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亦采取“先抑後揚”的态度。與 1980 年“鉛工業協會有限公司訴環保局案”中對《清潔空氣法》第 109 節的态度截然相反,在 2001 年“Whitman v.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案中,法院通過肯定環保局實施風險規制的必要性和行使裁量權的可能性,對成本效益分析在制定法中的缺失予以充分彌補。
當前我國已有少數環境案件初步适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如法院在“泰州 1.6 億元污染環境案”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訴北京多彩聯藝國際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大氣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案”中均肯定虛拟治理成本法在“治理修複費用難以準确估算時”的适用情形。雖然《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第 A2.3 條已簡單闡述“虛拟成本治理法”的内涵,司法實踐中利用“虛拟治理成本 = 單位治理成本 × 污染物排放量 × 環境功能區敏感系數”進行公式計算,但由于我國缺乏将自然資源保護币值化的司法經驗,而生态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不僅包括“已經到來具體危險的抵抗”,還包括“對環境有危險性行為的預防”和“對未來美好環境采取預先的保護措施”。以虛拟成本治理法為代表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卻忽視了功利和效率以外的道德因素、社會公平與正義等其他層面的意義,計算過程與結論分析的客觀中立性不足,因此隻能在有限度的、謹慎的情況下适用。加之生态環境損害的瞬息萬變和損害價值的難以估算,生态損害數額、範圍、利益屬性、責任歸屬等都可能因規則的創新性、政策性和不确定性而在裁判時産生巨大偏差,僅具有有限理性的法官難以在法律解釋的過程中進行整體性、明确性及事實統一的法律适用。一個完整的司法證明過程通常包括證據獲取、證據篩選、證據鑒别、證據推理、法律拟制五個環節,其中證據獲取、證據鑒别和證據推理環節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法官憑借經驗、技術收集與處理信息的對于揭示案件真相至關重要的自然過程。環境司法中證據獲取和證據鑒别均可以得到行政機關、司法鑒定機構及相關領域專家的科學性引導和支持,但證據推理仍考驗法官個人的經驗判斷和靈感直覺,所以法官在利益衡量過程中強調謙抑性并以“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為重要參考依據将是其進行實體裁判的最優選。
相較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實體利益調整型”能動模式的局限性,“技術(程序)調整型”卻可充分發揮法官積極主動創造性,同時亦能有效約束并抑制法官運用經驗或法理想象力的主觀恣意。如果“實體利益調整型”主要涉及實體層面法院、行政機關及被提起訴訟當事人之間利益和作用分擔,那麼“技術(程序)調整型”則主要通過法官在個案中主動完善生态損害賠償訴訟程序及相關聯程序設置、法院與行政機關程序聯動等“程序能動”方式,間接調整當事人利益關系以達實質公平正義。“程序能動”在不健全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有極為特殊的廣泛環境公益保護價值。由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行政權實施中的“監督強制職責”和對生态環境損害的“及時補救程序”能夠使受損環境恢複至初始形态,加之“政府作為責任強制主體”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多中心”型國家環境治理體系的應有之義,訴訟過程對實體利益分配的過度幹預易導緻“司法權越界”之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是我國環境司法的新事物,無論是制度設計抑或司法實踐尚處于實驗期,并且其程序運作非常冗雜且極具風險性,如技術性環境損害鑒定評估程序即橫跨行政與司法兩個階段,它作為訴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有效性、完整性及其在司法程序中如何适用、适用界限、被告人如何進行質證均無法律明文規定,而縱觀《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大部分程序性規定須“參照适用”,其訴訟程序特殊性與獨特性難以彰顯。所以相較于一般公益訴訟,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尤其需要保障被告基本的程序性訴訟權利,通過法官對程序鍊條全面化和極緻化完善,彌補具體法律規定的欠缺,實現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間非訴與訴訟程序的無縫對接,最終實現生态損害賠償司法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最初源于英美法系,強調裁判過程與程序的公正性,在 1853 年“Dimes v. Proprietors of Grand Junction Canal”及 1924 年“Rex v. Sussex Justices”案中,宣稱司法活動應遵照“自然正義原則”與公開固定程序下推進的“程序正義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将程序正義分為純粹的程序正義、完全的程序正義以及不完全的程序正義三種類型,并依據正義理論将程序正義看作評價制度正義的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标準。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前提和基礎要件,在實現程序正義的前提下追求“特定案件、特定處理”的實體正義,不僅有利于個案正義的實現,更是環境公共利益維護的應有之義。訴訟程序本身應有自我矯正和自我調節功能,既體現在實體事實确認中的審查過濾、對抗辨析功能,還體現在程序制裁和權利救濟功能。但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程序自治”遠未達到适當彌補實體規則、促進環境司法公正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統一的程度。因此我國環境司法未來可借助訴訟框架與結構中的“程序能動”以尋求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之間的相對平衡關系。
(三)“程序理性”之實踐缺口
在傳統環境法實施框架下,法院的謙抑中立性難以承擔生态環境損害填補和風險防禦的重任。司法裁判的謙抑性意味着,法院在很多情形下隻能依據法條規定“就事論事”,缺乏要求規制機構創設體系化、有序的規制規則的能力,并且環境案件具有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化特質,“以結果為導向”的實體利益衡量模式難以适應生态環境損害的不确定性和環境利益複雜多元性的司法能動需求。但法官對于環境風險、技術信息的預測、解讀和判斷并不比公衆具有更為優越的知識資本,法官在裁判過程中需要高度依賴行政機關就環境信息所做的專業判斷。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程序能動”需要法官在環境法律框架内适當積極地對預防性、修複性及相關銜接性程序予以拓展适用,以彰顯環境司法的終局性、權威性和公信力。當前,我國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程序理性缺失。
1.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協商性程序适用規則不清晰
環境司法中的協商性程序是當事人訴權的拓展和延伸,也是協商民主理念下多元共治、合作對話的現代型糾紛解決方式的重要體現,協商性程序強調公民以對話、協商為中心主動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體現程序自由價值。當前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協商性程序主要包括司法解釋明确規定的訴前行政磋商程序及法律未明确規定的環境司法訴訟調解程序。行政磋商屬于具有司法屬性的協商行政的範疇,是指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時放棄傳統行政處罰、行政代履行等約束性規制手段,通過行政性合意的達成消除雙方的沖突與分歧,促使相對人在形式平等的狀态下及時履行義務。相比較而言,訴訟調解是我國司法模式特有的産物,根據《民事訴訟法》(2017 年修訂)第 9 條的規定,法院調解應本着“自願”和“合法”雙重原則,在雙方當事人平等充分對話的基礎上進行,這與行政磋商在參與形式上有共通性。盡管《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 25 條認可調解作為一種結案方式,但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調解是否可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仍存在較大争議,并且由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的效力位階和定位問題還存在着規則模糊,實踐中出現“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失敗後提起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适用調解結案”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失敗後轉而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适用調解結案”的情形。比如“紹興市生态文明促進會訴新昌縣某膠囊有限公司、呂某和新昌縣某軸承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案”是由于行政磋商不成,案件轉入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後,法院适用訴中調解程序并以調解書形式結案;而“貴陽市生态環境局訴貴州省六盤水雙元鋁業有限責任公司、阮正華、田錦芳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山東省環保廳訴山東金城重油化工有限公司、山東宏聚新能源有限公司土壤污染責任糾紛案”及“汀溪水庫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交通事故導緻水污染事故索賠案”卻是在磋商失敗後,行政機關直接提起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并适用訴中調解結案。以上兩種情況延伸出多個不明确的程序銜接點,如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調解的适用順序問題、訴前調解能否适用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等。
2.環保訴訟禁令實施程序呈現地方“各自為政”态勢
環保訴訟禁令的實質即“環境司法提前介入程序”,通過向法院提出申請的方式,被侵害人可通過“不利後果擴散前”的民事救濟權利,事先避免個人财産或其他權利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禁令具有緊急性、臨時性和即執性的特點。一般來說,法院簽發禁令後會立即執行,這種立即執行性能夠在不利結果發生或擴散前起到臨時性強制措施的作用。2012 年 8 月,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制定《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環保司法訴前禁令試行辦法》,創設環境侵權案件訴前禁令制度,在傳統财産和證據保全外增加“行為保全”,并以行政機關或公衆主動申請為啟動條件。早在 2008 年,無錫市人大制定的《無錫市水環境保護條例》第 60 條“法院訴前強制措施裁定權”即展現環保訴訟禁令的雛形。以此為基礎,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于 2009年制定《關于規範環保行政行為職能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态資源等違法行為采取強制措施案件審查程序的指導意見》,并将訴訟禁令逐步應用于環境行政審判領域,明确具體的審查标準及适用程序,包括行政執法機關為申請主體、适用于行政非訴審查案件等内容。目前我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中并無訴訟禁令的相關規定,實踐中的具體實施規則均散見于上述各地方的規範性文件中,存在着程序啟動方式不明确、适用範圍不統一、審查标準參差不齊等多重問題。在“萬州市環保局訴萬州保傑廢油回收有限公司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環境保護令案”中,法院創新采用“環境保護令”這種最高人民法院訴訟文書樣式中并不存在的文書樣式和标題,同時案件裁定中适用“被告違法生産經營”的“違法性”司法審查标準;而在其他保全裁定案件中審查标準卻變更為更加嚴苛的“侵權性”标準,隻要行為人具備“在風險分析基礎上繼續進行損害行為”的可能性,法院就有權事前裁定訴訟禁令。訴訟禁令程序設計的終極目标在于通過司法提前介入環境行政(比如司法審查)的方式,實現環境司法的預防性效果,及時避免難以彌補的損失的發生或擴大而采取的措施。
但就當前生态損害賠償訴訟中禁令制度的實施效果看,僅體現出環境司法權“能動超限”并企圖“代替”甚至“僭越”行政權,沒有充分彰顯司法審查對于行政執法的訴前監督協助及環境司法的程序預防功能。
3.環境損害司法鑒定之中立性與證據能力不足
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是法官審判程序事實認知活動的延伸,司法鑒定機構及機構專家的客觀中立性與司法鑒定活動的質量、環境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密切相關。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發布《關于将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納入統一登記管理範圍的通知》,明确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的适用領域、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審核登記規定及監督管理措施,并确定由原環境保護部會同司法部建立鑒定機構和評審專家庫。環境損害司法鑒定與環境損害評估是屬性不同的兩個概念,環境損害司法鑒定不僅包含鑒定人運用環境科學技術或專門知識對環境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别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還需鑒定人對生态環境損害的後果進行數據統計量化評估并給出确切值。因此它是貫穿整個訴訟過程、确定法院具體審理内容與案件事實确認、責任分配的關鍵依據。根據《生态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 6 條和第 10 條的規定,原告行政機關有權訴前委托具備環境司法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并可作為事實認定依據。而在實踐中,原環境保護部在 2014 年和2016 年先後推薦的 29 家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機構及國内部分地方司法行政管理部門在各自管轄範圍内批準的 58 家具有環境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均具“公權力屬性”,因此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行政機關出具的鑒定意見作為證據的真實有效性飽受質疑。同時其專業性和技術性過強,我國專家證人的制度也不完備,導緻被告難以推翻鑒定結論和環境損害評估報告,被告質證過程與“申請重新鑒定權”亦難得以保障。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79 條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 28 條的規定,“當事人有權質證并申請重新鑒定”。但據統計,在 2015 年 45 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沒有一則案例顯示被告人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提出對環境損害賠償數值進行重新鑒定的請求。而在“山東省生态環境廳訴山東金誠重油化工有限公司、山東弘聚新能源有限公司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法院在省級行政機關提起訴訟的前提下,仍依職權另行聘請三位咨詢專家參加庭審并出具“損害賠償責任分擔的專家咨詢意見”,更進一步加大被告對鑒定意見的質證難度,被告在訴訟中享有的平等訴權難以得到有效充分的保障。
五、“程序能動”與“實體謙抑”結合之路徑走向
(一)基礎實施路徑
我國環境司法具有明顯的整體性特征,這是生态環境整體保護與統一裁判尺度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司法保障意見》中提出“構建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審判之間協同審判機制,充分發揮環境資源審判合力”,即囊括統一審判機構和審判程序在内的“環境司法專門化”改革訴求和方向。2007 年,我國首個環保法庭成立于貴陽清鎮市,并率先以打破行政區域限制的管轄方式審理“兩湖一庫”水資源保護案件。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目前我國環保法庭已跳出傳統的審理、審判與執行分離機制,呈現包含司法層面的整合,在一個審判組織内實現生态環境的整體保護與環境侵害複雜性、擴散性的共同應對,“多元整合主義”成為環境司法的基本立場而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在案件管轄方面,各地方法院主要以 “生态環境的自然屬性”“集中管轄”“協議方式”實施環境案件的跨區域管轄制度,卻以“類案指定管轄”作為分配數量巨大的環境案件的主要方式,違背了指定管轄的本意、程序法定原則及管轄權的基本要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據。(2)在訴訟程序方面,環境案件合并審理僅僅是案件類型的簡單組合,遠未達到環境案件多重法律關系屬性所要求的刑事、民事、行政訴訟裁判程序規則的實質整合。如“三審合一”或“四審合一”案件審理順位規定不全面、當事人陳述次序不清、法院能否主動調查取證及證據的适用問題等。(3)在判決執行方面,環境案件執行程序并無有别于一般行政/刑事/民事案件的特殊制度設計,沒有體現案件本身對環境可持續發展與生态修複的重要作用,比如植樹造林、淨化水質這類替代性執行方案的應用較少。(4)環境司法與環境行政聯動界限不明。環境司法的本質屬性是被動性、裁判性,環境行政的本質屬性是主動性、執行性,因二者本質屬性的不同,有時會出現“聯而不動、協而不調”“司法權過于強化”或“行政權配合司法權”的情況。
在此背景下,發揮環境司法整體作用,構建“程序能動”與“實體謙抑”功能導向下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是實現環境司法改革與專門化進程之核心要素。一方面,自《試點方案》發布以來,我國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體現出“漸進式”環境法治發展道路,其中“賠償權利人範圍的擴展”“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協議法律強制效力的增強”等突破性的具體制度實施内容,均彰顯出我國公權力機關在打擊生态破壞與環境污染違法行為方面的堅定信念。另一方面,環境監管執法的現實卻不容樂觀,經濟挂帥、環保理念的缺失、環保部門相對于經濟管理部門的弱化、職能不清、權責不明、行政處罰力度不足等問題導緻環保行政機關權威難立、執法不暢。有鑒于此,本文認為,有關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件價值判斷、利益衡量等實體問題宜采用謙抑、中立的司法态度,而涉及訴訟程序與結構等相關問題宜采取較為積極、主動的司法态度,在程序設置上盡可能發揮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預防性和填補性功能。
1.“實體謙抑”——注重我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在環境法領域的應用
我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是“統一法律适用尺度、填補法律漏洞”的重要方式,最早于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中提出。2015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對相關适用标準與适用程序規則加以明确,截至 2019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 20 批 106 件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檢察院共發布 13 批 51件指導性案例。指導性案例具有準法律淵源地位并可參考作為“裁決案件理由”與“司法适用标準”,各級人民法院認為不應參考的可在裁判文書的說明部分中闡釋理由,這類似于德國司法制度的“案例背離報告制度”。近年來,随着環境司法專門化與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完善,生态環境案件指導性案例得以被重視。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 75 号“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甯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在明确“綠發會是否具有起訴資格”的原告法定身份認定方面具有積極作用;最高人民檢察院 2017 年發布的第八批指導性案例中包括五起環保領域案件,在“福建省清流縣人民檢察院訴縣環保局不依法履行職責案”中确認人民檢察院“提出訴前檢察建議後繼續跟進”的督促依法行政職責。與之相比,目前最高司法機關發布的典型案例數量和覆蓋範圍卻遠超指導性案例。自 2014 年 6 月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先後發布 15 批 135 個環境資源典型案例,其中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典型案例共 6 個(表 5)。盡管典型案例也為證據運用價值權衡、舉證責任分擔等實體性法律問題提供參考依據,但其對下級法院的約束力遠不如指導性案例,“下級法院在審理與典型案例訴因相同或案情相似的案件時是否必須參照典型案例”“原告或被告是否可援引典型案例作為質證與辯護理由”“法官拒絕援引時是否需要說明理由”等并未有明确規定。綜上,有必要在環境司法中确認典型案例的适用方式和規則,并強化指導性案例作為環境司法實體利益衡量重要依據的絕對意義。由于當前我國法官缺乏審理專門環境案件的經驗,所以在遴選生态環境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時,應注重涉及“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多重法律關系時證明責任的分配與轉化”“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衡平”“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适用”“ 因果關系的認定和污染損失大小的衡量問題”等涉及當事人切身環境利益的關鍵争議點,構建符合我國環境司法整體思路的特色案例指導制度。

2.“程序能動”——注重以程序為取向之司法審查
法院對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的司法确認即法院審查磋商協議是否有效的程序規定,其本質是法院對行政機關契約行為的司法審查,審查後協議将被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由于環境規制具有高度技術性和利益多元性的特點,法院對磋商協議進行司法審查應盡量尊重行政機關實體性裁量權和規制選擇。磋商協議的性質屬于“行政契約”範疇,行政主體具有對行政契約履行的監督權、單方面解除優益權及對當事人不履行或不當履行合同的制裁權。鑒于磋商協議涉及損害賠償責任多少、不同當事人間責任分配方式、生态修複啟動時間、修複期限、修複效果評估标準等行政裁量所涉領域,需要行政主體根據法律規範所設定的範圍和限度,按照專業化理解對相關事實作出判斷和利益分配,此時法院應給與行政機關一定自由裁量空間并對磋商協議的司法确認進行以程序為取向的司法審查。值得注意的是,要把程序性問題與實體性問題區分開來。美國司法審查中“行政程序的強化”使司法機關對實體性問題行政裁量保持克制謙抑的姿态。1946 年,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中通過“行政決定前通知利害關系人”“舉行聽證會”“告知當事人權利”等正當程序性規範督促行政機關合理行使權力,隻要行政機關做到“程序無瑕疵”,無論事實裁定還是行政決定,司法機關在審查時一般都會予以尊重。由于在某些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件中,法院不具備行政機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又缺乏明确的法律規定以衡量行政裁量權,過度規範行政裁量權将對行政效能産生消極影響,由此法院對磋商協議實體内容的司法審查應保持謙抑、克制的态度。法院對程序性問題進行審查,一般有“對作出行政行為的程序”和“對判斷過程”進行審查兩種方法。此時,法院并不介入實質的權利義務分配決定,但借由程序的要求(例如行政機關是否在磋商過程中賦予當事人充分表達的自由)進行審查,在程序面上強化了司法的功能。如此,法院在“行政機關的風險衡量優勢”與“行政機關有限的裁量權力”間尋求平衡,确保行政機關嚴格遵守法律、避免恣意裁量。3.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行政執法聯動中加強預防性程序之适用。
環境司法與環境行政聯動模式能夠有效克服環境行政執法中長期存在的條塊化分割式部門主義及“政府失靈”的弊端,特别是在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案件中,環境司法之“協助”能夠在法定權限内合理平衡行政機關與被告一方的不平等法律關系,加之相對一緻的程式化運作模式的運用,将進一步增強公衆對環境行政機關及時、有效、公正地解決案件的信心。二者聯動的具體内容主要包括“法院受理案件後環境行政執法的啟動制度”“法院和行政機關的證據材料共享制度”“生态環境損害修複結果的行政機關協助審查制度”“司法建議推動環境行政執法制度”等。其中,非強制性的環境司法建議對“強化行政權積極行使”起到重要作用,其适用在近些年呈現出明顯遞增趨勢。2008 年,雲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曾出台《關于建立環境保護執法協調機制的實施意見》,包括“環境保護執法聯絡員制度”“環境公益訴訟證據支持制度”“環境行政處罰案件司法執行制度”等,但其實質仍表現為國家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外在形式組合。為改善聯動的“形式窘境”,應特别加強二者合作規制中預防性程序的适用,并明确環境訴訟禁令制度的法律地位、具體适用内容及運作程序。在美國環境司法實踐中,環境訴訟禁令兼具“臨時保全手段”和“及時救濟措施”的雙重身份,環境案件中采取禁令結案的案件數量遠超未使用禁令的案件數量。日本民法雖未明文規定禁令制度,但為實現“防止公害于未然”環境保護訴訟目标并應對日趨嚴重的環境公害案件,禁令請求已普遍成為環境污染受害者的重要訴求,法院對此進行實質審查并作出司法裁決,具有代表性的相關判例包括大阪空港公害訴訟與國道 43 号線公害訴訟、名古屋新幹線訴訟以及厚木基地、橫田基地噪音禁令訴訟等。日本國立景觀訴訟案中将環境公共利益權作為與物權、人格權并行的保全制度的權利來源。禁令制度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作用是對正在發生的嚴重違法行為或者侵權行為進行即時幹預和糾正,在最壞的生态環境損害結果發生前使失常的秩序恢複到常态,避免造成或者擴大損失。我國民事訴訟法律中目前還沒有建立完整的禁令制度,在屬性方面禁令制度體現為《民事訴訟法》(2017 年修訂)第 100 條“行為保全”的若幹要求,但環境訴訟禁令是否完全适用上述内容,其制度體系和規定還存在不完善和不健全的情況。因此,在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能動程序構建中,應明确環境訴訟禁令訴前程序的法律地位,并規定環境訴訟禁令的适用條件和範圍、申請方式與要求、審查标準和發布标準、中止發布的具體規則等。
(二)拓展實施路徑
在實施程序上,法院積極主動性的發揮離不開具體翔實程序規則的适用。比如涉及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共通性的“既判力擴張與已決事實免證效力規則”,人民法院在受理同一污染環境或生态破壞行為提起的此二類訴訟後,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中止審理期間,如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已決事實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待證事實屬同一事實且前後訴程序類型相當的前提下,法院對後訴事實可直接認定,并就後訴中未被前案涵蓋的訴訟請求依法作出裁判。同時兩訴當事人特别是原告方當事人之間可共享彼此所有的證據。就法院而言,其在一訴中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的證據,在該證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且“已經當事人質證且被法院作為裁判依據”的前提下,同樣可在另一訴中加以使用。此外,相關程序規則應包括但不限于:
1.協調發揮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與環境司法訴訟調解之制度合力
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與環境司法訴訟調解均屬“有效參與、充分對話”式協商性訴訟程序的範疇,但二者在屬性和适用方式上具有本質區别。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實質是“不平等主體間的行政協商”,即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放棄傳統的命令或直接強制執行,而采用商談、說服、誘導、勸誡等合作性、平等性與對話性方法,訴訟調解本質則是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與法院對抗式庭審模式相比,調解是在當事人地位相對平等、自願的基礎上,通過雙方直接交流與對話促進各方的妥協與利益認同,增進彼此理解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赢。由此,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屬于訴前強制性程序,在磋商過程中賠償權利人行政機關始終占主導地位,賠償義務人需要密切配合權利人進行磋商;而司法調解在民事案件中既可以由當事人申請也可以由法院依職權啟動,與司法判決相比更能體現出法的靈活性、高效、低成本、徹底性等價值。由此可見,在适用位序上,具有行政屬性的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相較于訴訟調解更具優先性;在适用範圍上,環境司法訴訟調解則可同時适用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一方面,此兩類訴訟均具民事屬性,在調解時均須遵守雙方當事人平等和自願的原則;另一方面,兩類訴訟原告均是代表環境公共利益的當事人而非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原告均享有“有限”的實體利益處分權和調解程序決定權。如在調解的啟動時間方面,由于生态環境損害具有累積性、間接性和潛伏性,往往需要時間積聚和累變才能發揮作用,而案件本身因果關系複雜,損害結果多元,隻有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調解才能在根本上保護環境公益。綜上,在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應是在法庭調查階段經過舉證質證程序後啟動的訴中調解。事實上在涉及公害的案件中适用調解 ( 或訴訟和解 ) 已成為諸多國家的制度選擇,如德國在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逐漸确立了環境團體公益訴訟制度,雖然性質上屬行政訴訟,但在審理案件時仍可由接受過調解訓練的法官主持訴訟調解。以此為基礎,通過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訴中調解(或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訴中調解)彌補生态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實質平等”不足,同時法院應對磋商或調解後的生态環境修複效果進行定期監測、監控與評估,使前置性的磋商程序與後續訴中調解程序的銜接發揮保護環境公益的實效性“共治”效果。
2.重視專家的訴訟參與
專家參與是提供專業化、技術化智力支持的過程性參與。從本質上說,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是“不同知識彙集、交鋒、選取并得以運用的過程”。相較于傳統的環境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基于原告的特殊性和其本身的預防性特質更有利于環境正義及公衆環境利益的大範圍實現,此時專家理性在解決環境案件的專業性、多樣性和複雜性方面發揮着無可比拟的作用,并且專家獨立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機構和人員的中立性不足等問題。一方面,環保專家可就審判實踐中所涉及的污染物性質、生态環境遭受損害的範圍和程度、因果關系作用原理、污染治理成本、防止損害擴大及修複生态環境的措施等專業性問題,向合議庭發表同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有出入的認定和參考依據;另一方面,環保專家可獨立對案件事實、技術證明等相關問題開展社會調查或實地調研,在特定情形下甚至會推翻決定性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目前,我國專家參與的主要類别為咨詢專家、專家證人和專家陪審員,相較于前二者,專家陪審員對法官裁判與案件走向産生最直接且根本的影響。雖然專家陪審員的核心任務是協助法官對專業性問題進行認定或駁斥,但其是合法的法律運用者和裁判者,擁有最終裁決權。而專家證人則是具有專業知識、了解案件情況但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特殊證人。專家證人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中是一個與普通證人相對應的概念,根據英國 1999 年《民事訴訟規則》第 35 章第 2 條之規定,“專家證人”是指為法院訴訟程序目的實現發表意見或提供技術證據的專家。在“山東省生态環境廳訴山東金誠重油化工有限公司、山東弘聚新能源有限公司生态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中,法院同時結合咨詢專家和專家證人參與模式,使當事人的證據能力得以充分利用。當前我國《民事訴訟法》(2021 年修正)及相關環境訴訟規範性文件中并無專家參與的詳細規定,相關規則體現于地方性法律文件中。比如《湖北省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中規定環境資源專家應盡可能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全程審理。所以未來我國立法中應明确專家參與的地位作用及适用情形、專家的選任方式、法院依職權請求專家出庭的條件等具體規則,法院在規則适用中也應盡可能擴大專家參與的适用範圍,充分保障當事人訴權,并加強案件事實調查的專業性、科學性和真實性。
3.加強多樣化“生态修複性”之司法運用
不同于傳統的“填補性”環境司法,生态修複性司法模式涵蓋着風險預防與生态倫理基礎的價值考量,并具有兩個重要特色:其一,責任承擔方式的多樣性。生态修複範圍從森林、水流、礦産等領域,逐步向海域、灘塗、大氣等領域拓展,并探索包括行為罰、生态修複責任、替代恢複補償等在内的與刑事制裁、民事賠償、生态補償有機銜接的環境修複責任種類。2017 年,福建省發布的《生态司法保護狀況綠皮書》中顯示其已形成“多層修複、立體保護”的生态修複新模式,全省法院适用“補種複綠”案件 199 件共 240 人,發出“補植令”“管護令”“撫育令”等 175 份,責令涉林刑事被告人補種、管護林木面積約 4402 畝,放養魚苗 516.11 萬尾治理水域污染 , 将“重懲罰更重修複”的無害正義理念融入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其二,修複模式的多樣性,包括政府運行、法院運行和第三方市場運行三種模式。其中,第三方市場運行模式最能體現生态環境修複的公益屬性,主要指由獨立第三方負責生态環境損害賠償款的管理并通過訂立協議、招投标等市場方式委托市場主體對被破壞的生态環境進行修複,而法院負責整個修複程序的“全過程監督”。但是,目前我國生态修複性司法存在法律依據不足和規則體系不完善現狀,在實踐中存在“異地補植”一刀切現象、缺乏統一的生态修複資金管理制度、法院對于修複責任的落實追蹤和驗收程序不完善等問題,由此,生态修複性司法亟須生态損害後的主動性司法,在司法權限度内将第三方市場主體納入其中并規範專項資金管理制度,最終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生态修複模式。



